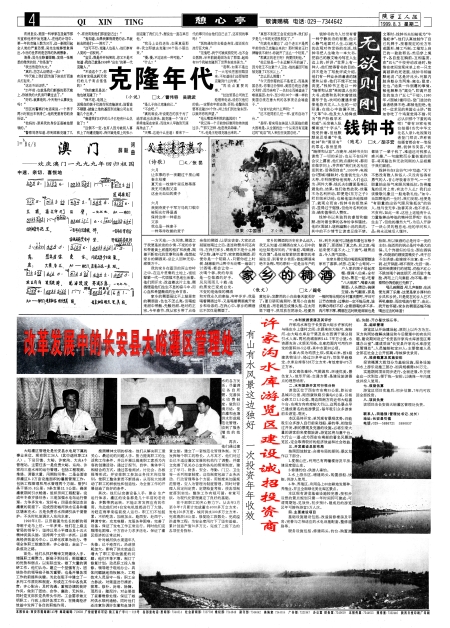
家乡的稠酒(散文)
文/阎冬
一方天地,一方风情。稠酒之于我便是浓浓的乡情,不变的乡音和带着黄土底蕴的粗犷和浪漫。隔着不断变化的世事和沧桑,每想起家乡的稠酒来,总让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
我的家乡在蓝田的深山穷岭之中,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祖祖辈辈一代一代顽强不息地生活着,他们用汗水,改造着这片土地。稠酒便是他们生生不息的奋斗中,用心血和希望酿成的生命甘泉。
家乡的稠酒虽比不上城里卖的稠酒甜,色也不怎么亮,但喝起来甜中带酸,先酸后甜,绝对的正宗。今年春节,我从家乡带了点母亲做的稠酒,让朋友尝尝,大家迟迟疑疑地喝过之后,连连称赞并问还有吗。在我们家乡,稠酒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逢年过节,家家都做稠酒,即便你是一个陌路人,只要你赶上时候,随意敲开山野中无论哪一扇柴门讨酒喝,都会让你一次喝个够。我的母亲是一位做酒的好手。风风雨雨几十载,她的黑发已变成白发,不变的是她做的稠酒和对我永久的牵挂。年年岁岁,我是喝着稠酒过年,又是喝着稠酒离开家乡和母亲的。在我心中,家乡的稠酒已不仅仅是稠酒了。
家乡的稠酒的历史有多么远久,我无从知道,但稠酒在家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是深知的。“听秦腔,喝稠酒,吃白馍”,是祖祖辈辈朝思暮想的幸福生活。别看家乡贫困,做起稠酒来绝不含糊,用的原料一定是当年产的黄包谷;发酵用的小白曲春天就买好了;夏日骄阳高照时,便用小白曲制成粗曲,用老碗压成馒头型,在太阳底下晒干,然后放在阴凉处。经夏历秋,到冬天就可以随意和着包谷糁子酿酒了。那酒纳了夏之热、秋之凉,喝起来便不温不火,上下通气,暖胃活血,令人荡气回肠。
在家乡最壮观的喝酒场面要数谁家有了喜事。试想,在某个山弯间,一户人家的院子搭起席棚,摆满八仙桌,全村老幼,聚在一起,吃着“八大碗席”,喝着大碗稠酒,人头攒动,碗碟交错,热气翻滚,那是—幅何等壮观的乡村喜庆图呵。平日可以节衣缩食,过事却一定不能马虎。谁的事办得好不好,全看酒喝的多不多,肉片厚不厚。稠酒在这时既是席面也是脸面。所以做酒的必是村中一流的主妇,烧酒用的锅必是村中最大的锅。几个馋猫似的后生,围在酒锅旁,和烧酒的嫂嫂耍嘴皮子,终于忍不住诱惑,趁嫂嫂不注意,拿一个碗,拉开锅盖,顾不得烫,先舀一碗,虽招来嫂嫂们的俏骂,仍脸不红心不跳地喝个碗底朝天,然后做个鬼脸,再吼上几句秦腔,你不喝,看一看那份馋劲就已先醉了。
喝几碗稠酒,吼几声秦腔,生活便充满了乐趣,这便是家乡淳朴的乡风和乡民。只是现在的乡人已不再吼秦腔,而改唱流行歌了,由此,我开始怀疑,家乡的稠酒还能不能喝出过去的味道?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