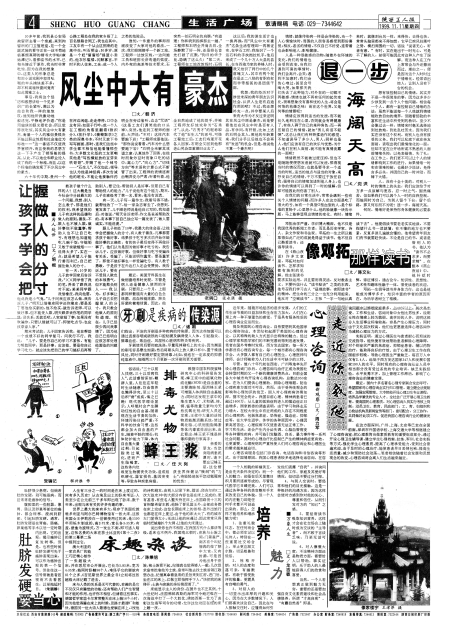
本版导读
风尘中有豪杰
文/朝济
30多年前,我到县公安局拘留所去看一个亲戚。来到拘留所的门卫值班室,见一个全副武装的看守正在一丝不苟地临摹颜真卿的楷书大字帖《麻姑潭记》。看那临书的水平,已相当接近于原作。我当时非常吃惊。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这类人的形象总是和旧小说戏剧中怒目吆喝的牢头捕快差不多;却不料高墙铁窗间竟有如此儒雅之士。
事后,我将这个经历和感想讲给一个见多识广的长辈听。满以为他会和我一样的地惊叹;谁知他听我激动地叙述完,平静地评价道:“你是用偏狭的眼光看社会,所以觉得很吃惊。其实风尘中大有豪杰。衡量一个人的雅俗贵贱决不能以职业性质和社会地位为标准……”这一番话不仅使我茅塞顿开,而且使我的思想方法一下子产生了顿悟般的提高。从此,不以地位和职业论人成了我的一个标准。而且,以这个标准的确发现了不少风尘中的豪杰。
六十年代中期,贵州一个公路工程处在我的家乡招了上百名修路合同工,我也在其中。工友中有一个从山区招来的老高中生,叫石明全,30多岁,原是一个赶“溜溜场”提篮小卖的。他衣衫褴褛,沉默寡言,平时不和人往来。工余,或一个人在河边闲逛,走走停停,口中念念有词,如屈子行吟;或一个人在工棚的角落里翻看《微积分》、《拓扑学》、《模糊数学》之类的深奥书本,不时又放下书写写画画。那时,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不相信他能看懂那些书,大多数文化低的工友更嘲笑他是“写些横起放的豆芽来哄哥哥”,并赐了他一个绰号——“石生儿”。不仅如此,领导,也认为他是神经病,多次告诫他的班长,不能让他接触炸药之类的危险品。
谁知,一件意外的事却彻底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一次,我们排刚接手一个新工地。工程师一边放灰线,一边向施工员和班排长讲弯道的弧度、内外弯的高差等技术要求。石明全在旁边偷听,边念“咒语”(这是工友们调笑他的口头禅)。突然,他走到工程师的面前,大声说:“不对!这样汽车要跑下岩!”工程师戏耍他说:“那你说说看看,汽车为什么想要跑下岩?”石明全未解其戏谑之意,认真地作了回答。在他时而象炒豆时而象口吃的话中:“离心力”、“向心力”、“切线方向”等术语和计算公式不断冒了出来。工程师的表情逐渐由嘲弄变为严肃;听着听着,他突然一拍石明全的肩膀:“有道理!你和我到指挥部去一趟。”工程师和石明全并肩去后,全场静默了好一阵。还是排长首先打破了沉默:“狗日的华子良,隐瞒了这么久!”第二天,工程师在工地改放线时,石明全自然地成了他的助手,并被工程师友好地戏称为“石秀才”。从此,“石秀才”的昵称取代了他“石生儿”的恶号。可惜工程完工后,工友们鸡蛋开花各人回家,石明全又回到他那老山旯旮里重操旧业去了。
这以后,我的谋生活计也一换再换,而“风尘中大有豪杰”这条生活哲理却一再被证实。在学石工时,我结识了一个运石料的手扶拖拉机手,他后来成了一个几十万人大县的县长。在当四海为家的养蜂人时,我又结识了同行中的几个落魄文人,其中有两个现在是正二八经的有职有权而非带括弧的县团级干部。
我想,我的经历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年朋友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是有启迪作用的吧?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并非要某人后来有大作为才反过来证明其在风尘中原是豪杰,而是要看他处在风尘中时是否有人品,有学问,有肝胆。比如上述的石明全其人,照他的年龄算来,我们分手以后他也不会再有“发迹”的机会,但是,谁说他不算一个豪杰呢?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