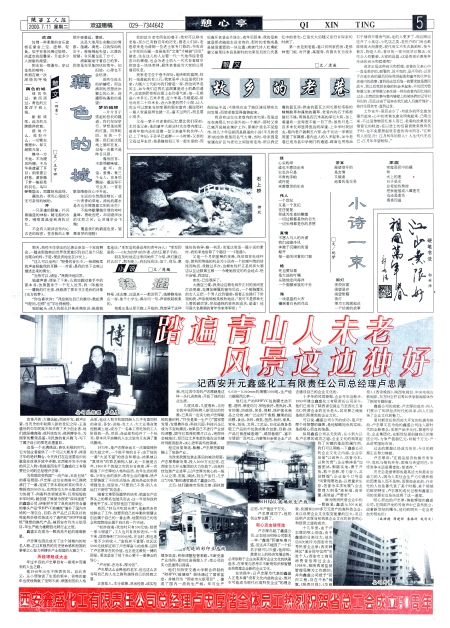故乡的老巷
文/清溪
我的故乡老宅所在的巷子,绝对可以称为老巷,至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据老人们讲,老巷原来是为清朝一位进士家专门修的,书有进士字样的石匾一直悬挂到“文革”才被破“四旧”破走。住在这儿的人总要一代一代地传说老巷昔日的辉煌。也会为进士后人一代代在衰败中把房舍一块块卖掉、最终老巷成为大家的公用巷而叹息。
我家老宅位于巷子深处,是砖砌的窑洞,同时一线盖起的有三孔,我家居中,东边是我们本家,大概六七代前与我们曾是一家,西边则早易其主。如今我们这两孔窑洞算是进士的最后遗产。这窑洞即使现在看上去仍很气派,每一孔都是八米多长、五米多宽、近六米高,冬暖夏凉,前后尚有二十四米长、近六米宽的两个小院,让人完全可以想象当初家景的殷实富有。据说那时一般人家盖窑洞也就一孔,富不过两孔,而且要小得多。
父母一辈子对老巷的记忆要比我们深刻,尤其是父亲,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在巷内度过。前两年巷内还生活着一位父亲童年的伙伴,人已上了年纪,子孙早已成群……小时候,父亲的父母过早去世,他是随叔伯三爷一起生活的,而后离开老巷出外谋生,成年后回来,我的母亲就是那次随他走进老巷的。那时的老巷尚是县城很重要的一块位置,离唐代诗人杜甫的舅父崔顼任本县县尉时的宅第及后世几代县衙旧址不远,不像现在由于城区建设朝东北向发展,而使老巷显得偏僻起来。
我没有出生在老巷内的老宅里,而是出生在离那儿70公里外的一个煤矿,那时父亲已离开县城在煤矿工作。那煤矿虽名不见经传,但几十年后却因是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原型而名气大增。当时,母亲因是家属在矿区与老宅之间经常走动,所以我记忆中的老宅,已是长大后随父亲归乡探亲的时候了。
第一次见到老巷,巷口有两家药房,是那种宽门板、对开窗、高屋脊、有兽头瓦当流水檐的蓝瓦房,拱曲的蓝瓦之间长着松塔般的辣辣酸草和蓬勃的蒿草。老巷内的石子路面破烂不堪,两侧是四五米高的深宅大院,加上巷道有一定弯度不能一目了然,虽然只是二百多米长却显得悠远而深邃。上中学时我回去,巷内老户就剩五六家,由于北边一家被征用盖了家属楼,巷内出入的人多起来。如今老巷已成为县中学侧门的通道,路面也用柏油石子铺得平展而气派,走的人更多了,而且路边还开了小卖店、小吃店之类,老住户的门房也都修得高大而漂亮、现代而又不失古典韵味。抚今看古,物是人非,昔日的一家兴旺早已散去,化作众人的繁荣、大家的昌盛,这是否预示着某种生活的启示和哲理呢?
或许正是这种启示和哲理,老巷在父亲心中一直是美好的、耐看的、说不完的、品不尽的,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仍给我讲起他和童年的伙伴在老巷内的故事,直到他去世后惟一的要求就是葬回故乡。那以后我回老巷的机会多起来,不仅因为要祭奠父亲,常常像父亲生前一样站在巷内回忆他的过去,总想把往事与巷内墙壁上的某块砖的记号对号似的,而且还由于母亲在我们成人后离开煤矿,独自住回老宅,直到过世。
工作在外,虽回去少了,对故乡的怀念愈加强烈起来,心中的老巷也愈发明亮起来、凸现出来,不过是借物回忆亲人而已。老巷的沧桑使我循着它的轨迹,在以进士的后裔衰败来教育孩子时,也不免要想起张若虚的诗中所言:“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