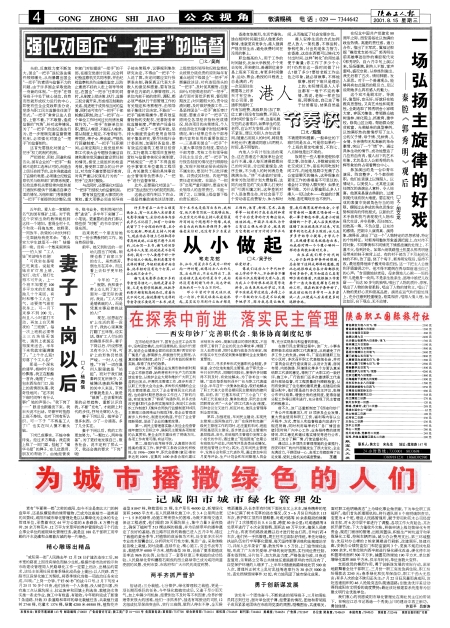
妻子下岗以后
□文/杨海信
五年前,爱人在一家颇有名气的国有煤矿上班。对于我这个农家出身的教师能找到这样一个媳妇,惹得全村十几个和我一同掏鸟窝、挖野菜、一同放羊、砍柴的小时伙伴们一见面就给我亮耳朵:“看人家大学生就是不一样!”结婚那一晚,没有一个敢来闹洞房——怕人家“工人娃”笑话咱乡巴佬!
可我实在是哑巴吃黄连。说起来她在矿灯房上班,发灯、收灯、修灯忙得不可开关,上一个班不知要在100多平方米的灯房里跑几十个来回,有时和哪个工人生了气,还要把气泄在我身上。可一月下来挣不到200元,而且八小时雷打不动,再加上白天黑夜的“三班倒”,每一次上班前必须带上三五块钱买饭吃,遇到上夜斑还得接来送去。半年下来我就牢骚满腹了:“上个什么班?穷落了个工人名?”
那是一个深秋的清早,杨树叶子纷纷飘落,我正在酝酿一首诗,她提了一大包东西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失落。我奇怪地问:“还不到下班时间呀!有什么事?”她的声很小:“我下岗了……”眼泪也跟着流下来。我半天说不出话,尽管平时抱怨上班不挣钱,也对下岗有所认识,可一下子“不再是工人了!”也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下岗已成事实,不能守株待兔。经过多方筹备,我在街上租了一间门面,挂起了“福华书屋”的牌子,在几位恩师、朋友的帮助下,由她经营卖书、租书业务,我利用闲时负责“进货”。多半年下来赚了一小笔钱,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从那些很“时髦”的书中学到了很东西。
后来我托一个朋友给她找了一份乡聘教师的工作。她当然很珍惜。
前年,她又到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当了阿姨,顺便也教了自家三岁的女儿,虽然清苦,倒也乐在其中。而且看上去似乎更年轻了!
今年的“五·一”假期,我和妻子带上女儿到了龙门,面对一望无际的黄河,我说:“工人不再是端铁碗的人,而是凭真本事迎接挑战的人!”
现在,回想起在矿上生活的那一段日子,我的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瓶。说实话,煤矿工人付出的的确很多很多。妻子下岗以后,听说那里又有不少人下岗,可矿上的形势仍然很严峻。一时人心惶惶。“下岗”一词在温州人眼里就是“站起”,而对于我们被秦砖汉瓦所保守,又被隋风唐韵所陶醉的关中人来说,下岗好像就是丢人,就是“栽倒”。应该看到改革的必然趋势,重新认识自我,不断“充电”,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抒写光辉的人生。
妻子下岗以后,她学会了很多东西。少了一分清高,多了几分实在。
妻子下岗以后,我的工作更加努力。“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服务社会,说不定到了那么一天,我还会真的要求“下岗”呢!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