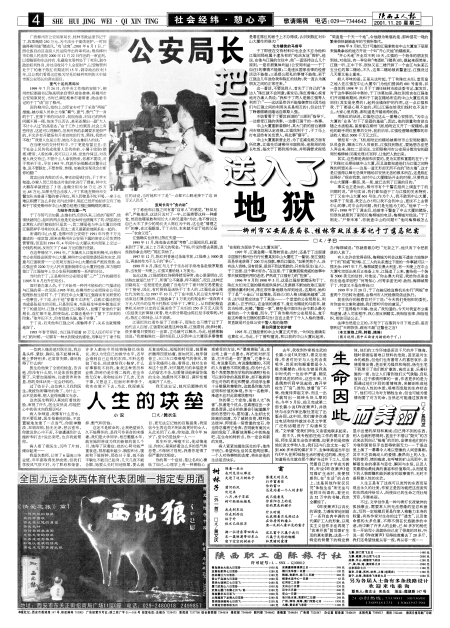生命因此而美丽
□文/奚同发
去年,我收到作家杨生武的长篇小说《凤阳堡》,看完后觉得,作者对历史与人生的含英咀华,其深刻和凝重都是令人极为震撼的。杨先生曾是我高中时代的一位治学严谨、颇见儒学风范的师长。这些年来,只是偶然听同学说起他,离开学校当了“官”。谁知,放着“官”不做,他竟侍弄起文学,而且一出手就写出一部砖头块儿厚的书。今年5月份,他又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昨夜箫声》,并很快与北京作家出版社签定了出版合同。这中间,我们曾多次通过电话和信件就该书及文学更广泛的话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文学缘”使我们师生又亲密地联系起来。
前不久,我专程前往他工作的铜川矿务局,师生见面生出些许感慨,但更多的是彻夜地长谈文学和人生。我们还与几位文友一起下到400多米深的煤矿井下,去体味路遥当年创作《平凡世界》体验生活时曾走过的路,我也才知道杨先生就在那个煤矿当过井下工人,后来凭着自己的才学成为教师。听说《昨夜箫声》是写煤矿生活时,我便预感到,在“生活”的占有上,这是其他作家仅仅凭“体验生活”所无法与他同日而语的。看完长达52万字的书稿,我完全震惊了。
《昨夜箫声》以诗化的语境,力透纸背地刻画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当代煤矿工人的形象,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再现了“改革开放”前后煤矿生活的真实原貌。这是一个特定的背景下的特定群体,他们的工作环境是深及千尺的井下煤海,随时都面临着难以预料的危险,甚至是对生命的威胁。但他们也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亲情爱情友情,甚至更为强烈和绚丽。杨先生笔下既展示了他们粗犷豪放、高尚正直、乐善好施的一面,也让人们看到他们义气狭隘、自私盲目、过于感情用事的一面。作者更多的是力图通过他们不同的爱情视角,来解剖形成他们内在人性的本质。艰难而危险的生存状态下,他们可以为对方牺牲生命,但也可能为爱情而要了对方的命,当然还可能通过放弃来显示出爱的深刻和真诚;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就别想得到,甚至于不惜以“毁灭”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极端”的目的,法律在他们的行为准则面前似乎也显得软弱无力……于是这里上演了一幕幕令人难以想像的人间悲喜剧。其中不乏哀婉动人的爱情、激昂向上的人生、死的惨烈、情的痴迷,在呼啸的矿山风雨中,注解着生命的凄美与悲壮、瞬间与永恒,以及人类最原始最纯真的善恶和价值取向。从而使笔下的人物群雕和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无时不普照着人性的光芒。
人生正是有了这些可以流传的东西而呈现出永久的壮美,作家正是因为能把这些流传的东西流传给后人,而使自己的生命之花吐纳芳菲,尽展美丽。
不过,文学创作是一种与青灯长夜做伴的孤独事业,需要常人所无法想像的坚忍和意志,写到一定规模后更是作家人格魅力本身的较量。有些作家对生命的过于“透支”,以及使命感的太多负重,不得不倒在长旅跋涉的中途,而中断了许多人的企盼。已50多岁的杨先生一开始写小说就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听说一部《昨夜箫声》写得他竟瘦去了20多斤,我们还希望他能从容一些,再从容一些……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