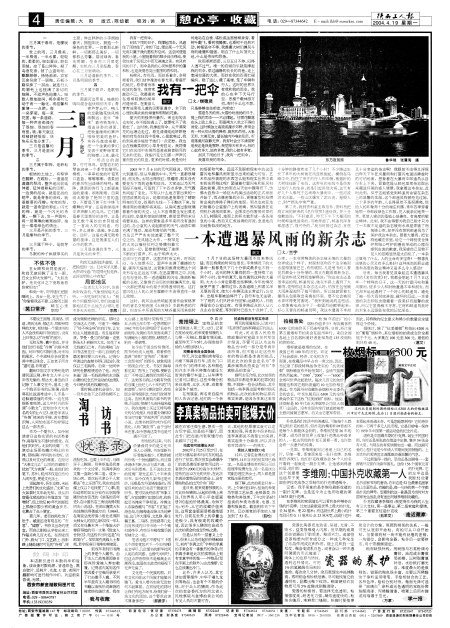
淘书访书
忧喜录
不要说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周氏兄弟、郁达夫、郑振铎那样的大家,相信每一个爱读书的人不会没有淘旧书的经历,没有上旧书店、访“冷摊”的爱好。
无权无势、囊中羞涩,并非他们访旧书逛“冷摊”的根本原因。对旧书的不期而遇,对未知的渴求,个中滋味非亲自置身其中难以体会,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
翻阅中国文学史特别是明清民国以降,鲜有文人学士与旧书无缘的。郁达夫、鲁迅的日记除了人事交往外,基本上是一个购买旧书的记账簿;钱杏邨在抗战逃难途中,几乎是一边躲避倭寇的炸弹,一边在拣拾断章残简。这几年时兴的所谓“小散文”,岂知如今大大有名的《浮生六记》,就是学者从“冷摊”拣来的手稿。若非慧眼识珠,人间怕永远不知存留过这么一部杰作。
作为一个爱书人,如今阅读昔日这些先贤的书话类著作,每每有生不逢时的感觉。在他们的时代,北京的琉璃厂、天津劝业场那些鳞次栉比的书摊,那些满口学问的书老板、店员以及对文化的尊重,在经历“大革文化命”以后的吾辈眼中犹如“天方夜谭”一般。在他们的笔下,苏州、杭州不仅是自然的人间天堂,更是文化乐土。
说起淘书,吾生也晚,未赶上先贤们的文化盛世,“文革”如火如荼时又年幼无知,没从归宿是化浆池的旧书堆里发“国难财”,但上世纪80年代初却赶上那段中国少有的黄金岁月,也算占了点小便宜。
那几年,老百姓刚吃饱了肚子,城里还没有现在的“市容”、“城管”,书价又出奇的便宜。而自己刚刚从学校出来工作每月有几百大毛,在西安西门外、西大门口、文艺路上、西影路上随处随时可见的“冷摊”,便成为频频光顾的所在。那时公交没这么方便,可座下一辆除了“铃不响全响”的自行车,让它的主人随意游逛。而且每有斩获。罗曼·曼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崭新四大本,仅花了4元钱就归己有,而在南院门古旧书店里往往一部几百页的长篇名著仅要三五毛钱。记得少年读过的查禁书《保卫延安》,我仅以三毛购得,后来一位同学研究杜鹏程便送给了他。而在朱雀门里一毛钱购得的东方既白著的纪念五卅运动的《血周》,今日绝对具有收藏价值。
那时候出差机会很少,但一旦外出住下之后那怕顾不上洗脸吃饭,也要上旧书店、马路牙子上瞅瞅。别林斯基是我喜欢的一个文论家,但满涛译的文集一直缺少第二卷,成为一块心病。首次赴天津公干人家都去“水上乐园”玩,我在劝业场楼上仅以7毛钱便了了心事。类似这样的如五分钱在北京购得降价的吉田茂的《游荡的百年史》,在中国书店三角钱购得《契诃夫小说选》,在湖北襄樊火车站地摊购得奥威尔的《1984》,在南京总统府旁小贩处觅得斯大林女儿的回忆录《仅仅一年》,后又在乌鲁木齐一个维族火炉旁获得她的另一文集《致友人廿封信》,而这些书当时还是“内部发行”,仅供某些高级人士参阅,若非现身旧书摊实难睹面。
前些年卖到旧书摊上的多是个人藏书,由于主人亡故等原因昔日那些珍爱被人弃如敝履,记得省内某知名作家因爱子空难而承受不了打击撒手人寰,不到半年盖有主人藏书印的书籍以废纸价成麻袋的被卖给收破烂者,我在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