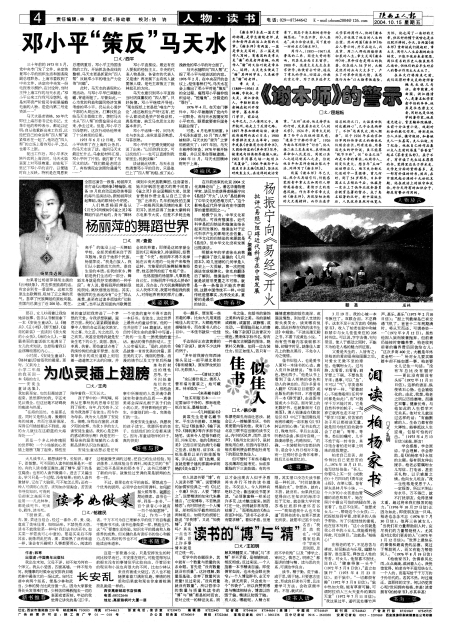
《谢本师》的警示
□文/屈超耘
《谢本师》本是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学生谢绝老师、表示和老师在政治上决裂的文章。《谢本师》有两篇,一篇是章太炎写的,另一篇是周作人写的。有意思的是章太炎“谢”的是老师俞樾,而周作人“谢”的又恰巧就是章本人。这样,太炎先生便成了“谢”其师的学生,又是被学生“谢”的老师。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年轻时因为俞樾在杭州开馆讲学,慕名拜其门学习,前后达七年之久,二人情同父子。离开杭州,他走上了反清之路。1897年参加维新运动,被清政府通缉而流亡日本;1900年剪掉长发立志革命;1903年发表《告康有为论革命书》,又因给邹容的《革命军》写序,被清廷勾结英租界逮捕入狱;1903年同蔡元培一起创立“光复会”,1906年被孙中山迎至日本主编《民报》,坚决反对改良主义。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因忠于清王朝的老师俞樾骂他:“不忠不孝,非人类也”,故尔和俞决裂,写下轰动一时的名文《谢本师》。
周作人,(1885—1967)是鲁迅的二弟,因受大哥的影响,同其先后赴日本留学。1908年,适逢太炎先生在东京讲学,他便前去听讲,遂成了章氏的学生。回国后,任教北京大学,写了很多进步文章。“五四”运动,他支持学生的行动,发表著名论文《人的文学》。1924年,因章太炎脱离了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退居于宁静的学者”,1926年南北军阀联手“讨赤”,他又接二连三发表通电,表明他离革命和人民更远,周便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仿效他当年和其师俞樾决裂之手法,同样写了《谢本师》。
两篇《谢本师》年已久远,然今天再读它们,仍能感觉到青年章太炎和周作人那种英姿勃发、豪情万丈的思想风貌。作为革命家章太炎的《谢本师》,再现坚韧决绝的大无畏精神。而作为进步文学家的周作人,他的《谢本师》,亦体现了他当时人生的企望。然而两篇《谢本师》给后人警示的,并不在这儿,而是章、周二人那戏剧般悖离初衷的人生。章太炎写《谢本师》时,革命信念是那么的执著,但在进入54岁时,大概是经历的血与火太多了,产生了对革命厌倦之情,其思想行为和“以大勋章做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几乎全是两样了。不但“远离民众,渐入颓唐”,还于1926年在南京担任军阀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礼仪制会会长。所有这些,用鲁迅先生的评价说,虽不能算“晚节不终”,但“白圭之玷”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周作人,则变化更大。想当年“五四”运动那当儿,确不失为新文化运动中一员猛将,曾几何时,到了54岁那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他摇身一变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的督办,成了臭名昭著的汉奸。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府虽然对他宽大为怀,他也写了一些好的文章,但汉奸的帽子说啥也是永远脱不掉的。今天,当两篇《谢本师》重新被我们提起时,章太炎、周作人人生后期的政治转变,不能不使后来者深思,两位有名的历史人物虽然早已逝世,但他们的后半生对后人的警示作用太大太大了。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前,我们还得对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先生说几句话。俞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爷爷。他虽是位忠君主义者,同时也是位饱学的著作家。他是道光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生前十分注重小说、戏剧对社会的教化作用。特别是他为人正派,操守极好,和妻姚夫人一生甚笃。夫人仙逝,为了纪念,他把自己的作品集以夫人生前的居屋“茶香室”起名《茶香室丛钞》。屈子不才,有幸读了先生这本厚厚的书,觉得里边关于学术史、文学史方面的资料甚多,是一部有价值的好书。然而,在中国风起云涌的十九世纪末期,他在政治上的保守和反动,对今天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有警示作用的。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