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前,敢捋文革“虎须”de关中愣娃

图为当年布告上的“囚照”和“罪行”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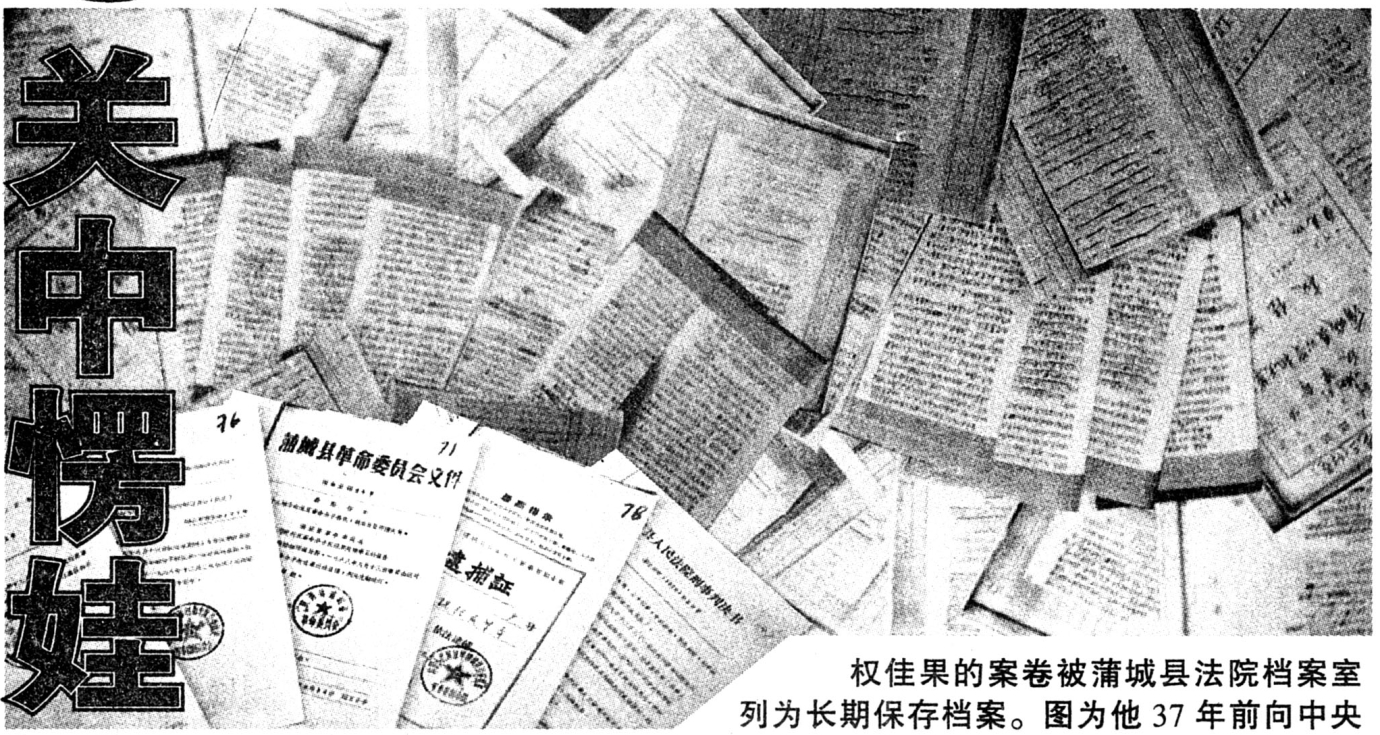
权佳果的案卷被蒲城县法院档案室列为长期保存档案。图为他37年前向中央“上书”的部分手稿和地县给他判刑、平反的部分文件。
(上接第一版)
第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在《认识》中尖锐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斗垮党内走资派,实际上斗垮了各级的主要领导。“问题不仅在于个别办错了事的当权派,而在于目前国家这整个管理机构,……在于我们党的一些错误政策。”他说:“大规模的武斗,营垒相对,枪炮相交,强行抢掠,行凶杀人……这些都是文化革命直接造成的。运动的领导者不是教导群众理智,而是教导群众蛮横;不是教导群众聪明,而是教导群众愚蠢……”最后,他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说:“以这样的政治家人工制造的运动,无论是文化革命运动,还是社教运动,或是以前以后其他什么运动,决不会把社会向前推进一步。”
第四,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反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他在《认识》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并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是许多人共同的思想。毛泽东的行动和言论最集中最全面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思想……”他激烈地抨击了神化领袖的做法之荒唐愚昧,指出当时把领袖“作为神圣,要人们像对待圣像一样对他跪拜”,“在我们的工作中实行着这样一个原则,即不问青红皂白,不讲去从由来,不问什么目的,不讲什么原因,只要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就坚决照办”等口号和原则的谬误。最后他疾呼,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旷古未有的、史无前例的地步。这种个人崇拜最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最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对于当时的造神运动来说,权佳果的这些话简直是一声霹雳!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观点,造成了他后来十一年的牢狱之灾。
离乡登程 风萧萧兮渭水寒
权佳果并不鲁莽,更不幼稚。带着这样的材料上北京,可能是什么样的结局,他心中是完全清楚的。他在《认识》的附录中写道:“最可能发生的倒是这样的情形,这就是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这就是监禁、杀害、各种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他的态度如何?权佳果写道:“如果谈到我个人,谈到我个人的生死存亡,那么我既决心将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我还有什么我个人的事情可谈呢?为人类的事业,无论什么时候死,什么地方死,我都是高高兴兴,视死如归。”
他已好几年未到亲戚家去了。1968年春节,他特意到舅家、姨家和姑家,给这些长辈拜了一次年。他想,这也许就是最后的诀别。
3月2日下午,他干完在生产队的最后一晌活;晚上,在他的小屋里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他把《认识》的副本和数十册日记、读书笔记放置在一起,把开屋门的钥匙挂在挂草帽的钉子上,又写了一张留言藏在草帽的下边。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家中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但又不能让他们很快就知道。这张字条是留给父亲和哥哥的,说他是“因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去一趟……请勿寻找。鉴于我已全身投入于政治之中,我既已将我整个生命献给为人类服务的伟大事业……我请你们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为我而奔走。在我的生活中是没有什么父子兄弟之情的,请你们也将父子兄弟之情忘却。”他希望尽量不连累家里的人,不要给家中带来太大的灾难。
3月3日天亮前约两个小时,他便起床了。上北京带的《认识》装在棉袄里子上特意缝的一个口袋里,隔衬衣正贴在胸前,使其不致丢失。他早已打听到渭南到北京的火车票将近20元,为此他把为生产队拉架子车外出干活挣的每日几角钱的差旅费积存起来,此时已有20元9角5分,想来够路费了。一切就绪,他便悄悄地离开了家门。
当他走出村子,回过头再于苍茫夜色中望着村子里模糊的土墙、瓦屋与那些尚未发芽的树木时,难免心中涌起一股感情的波澜:村中的父老乡亲们,佳果要走了,你们理解他正是为了千千万万苦难的老百姓,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去赴汤蹈火的么?还有熟睡中的白发老父亲、仁爱的兄长,你们知道佳果是怀着对人类的厚爱和忠诚而试图力挽狂澜的吗?佳果此去很可能要连累你们,还请你们原谅他吧。这时,权佳果又想起几年前已于贫病劳累中去世的母亲,不觉热泪已涌出眼眶:“生我育我劳苦受尽却未享受到我一丝回报的母亲啊,你早早去世,难道这竟是你的幸运?如果你今天还活着,当如何承受因我这次闯祸行将遭遇的打击啊!”
此时,惊蛰尚未到,拂晓前尤其寒气袭人。他不敢久停,只怕父兄发觉后追上来,便抄斜路快速行进,步行一百多里来到渭南。
夜里12点,他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上书”京华 “面君”不成沦“钦犯”
火车进入北京站已是4日午夜时分。他无处可去,就在站内一处水泥台阶上躺下来休息。阵阵寒气侵袭,他时睡时醒。挨到五点多钟起来,摸摸他的布袋,只剩下最后一个冷馍了。他啃完这个冷馍,等到天色发亮,就在一位扫马路的老清洁工人的指点下,向自己的目的地走去。
权佳果走到东长安街时,天已大亮。宽阔的街道上,行人与车辆稀少,颇有几分萧索的气氛。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当他走近天安门广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悬挂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的牌子。至此他才领悟到,扫路人为他指点的就是这个地方。也罢,一个普通百姓怎么进得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呢?此时接待站大门尚未开,他向南眺望天安门广场,只觉一片空旷,人民英雄纪念碑显得好像十分遥远。总之,1968年早春的北京,带给他的心情连同视觉的,基本上是一种灰色的调子。
终于等到接待站开门了。这里是清代的太庙,有红色的宫墙,高大的古柏,巍峨的大殿。但他无心观赏,径直来到登记处。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全是军人,因为当时全国到处都是实行“军管”。他们向他要介绍信,他没有;问他上访何事,他从怀中取出《认识》递了上去。那人不露声色地翻看了两三分钟,就把《认识》还给他,说:“你带上它到后边的第三殿去吧。”
到了第三殿门前,他发现挂的牌子竟是“保卫处”。他明白,那人让他到这儿来是要羁押他了,他在渭北家中所预料到的政治迫害就要成为现实了。此时他脑中根本没有出现离开此地的念头,他必须与他们争辩,把《认识》递交给中共中央。他几乎只思考了几秒钟,便毅然走了进去。
保卫处自然全是军人,他们翻看了权佳果的《认识》之后,便斥责《认识》是反动的。权佳果一再坚持要和中央领导面谈,他们却不予理睬,只是吼着说他思想反动,是反革命。听着这几位军人的“革命”呐喊,权佳果觉得非常可笑。一位中年军人恼怒地问:“你笑什么?你有没有什么病?”在他们眼里,这么一个西北农村的土老冒,竟想和中央首长交谈,竟敢批评文化大革命,甚至批评毛泽东,更奇怪的是竟然不怕危险自动找上门来送死,这小子不是患有精神病吗?
他被羁押在保卫处,天黑时又被送到一处收容站。当收容站与接待站的人办完交接手续后,权佳果被带到一所空房子中,被要求脱光全身所有衣服,进行了一遍搜身检查。连同衣领、衣角,都被细细地捏了个遍。权佳果怎么会想得到,原来这个收容站关的主要是小偷之类,他们把权佳果也当成了一个小偷,在搜查他身上是否藏着偷来的钱呢。这里,晚上在一个大屋子里的通铺上,每两个人被分配盖一个短小而又肮脏的被子,极为拥挤地睡在一起。白天两顿饭,每顿只有一个玉米窝窝头,显然玉米只磨了两遍而没过箩,玉米糁混着玉米面,甚为粗涩。另有半碗汤,清水煮菜叶,仅有一点儿盐味,管理人员公开声明是绝没有油的。
权佳果以为在这儿就要接受审讯,他等待着审讯时再作辩论。谁知九天后,他却被押解回蒲城。
权佳果的进京上书,就这样草草收场了。他后来曾幽默地说:“我是中国的唐吉诃德。”这个幽默,分明带着几多苦涩。
想来的确有些可悲;只不知愚蠢而且可悲的,究竟是权佳果还是当时的中国?
难道这就是权佳果应得的“待遇”?
“保留意见” 镣铐锒铛气浩然
3月15日,权佳果被塞进了蒲城县政府院内西侧的看守所。
5月初,终于等来了审讯。接连审问了几场,审判员说他的《认识》是反动的,他则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法庭的审讯笔录有如下记载:
问:“你认为你这个东西(指《认识》)正确否?”
答:“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
问:“你写的这个东西,有错误的地方没有?”
答:“我认为没有错的地方。”
问:“好,你的东西你认为既正确,首先你讲一下你的‘唯阶级观点’是指谁?批判的谁?有何根据?”
答:“我认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基本上没有阶级。”
审判员见无法让权佳果认错,就拿起“红宝书”念起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一段语录,念完后厉声问道:“主席的这段最高指示与你的观点之间,究竟谁说得对?”
当时的形势,谁敢说毛泽东半个“不”字!
然而权佳果明确地答道:“我认为,主席这一段提法不正确;我认为我国现阶段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态度鲜明,毫不退让。
主审官又念了一段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权佳果则平静地答道:“没有讲出什么道理。”
在最后一场审判将结束时,面对“你错了,就应认错、改错,否则你是罪上加罪”的诱导,权佳果仍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你们可以按我说的问题,定我的性质。政府无论判我什么罪,我在行动上都服从法律。但是,在思想上我要保留我的意见。保留我对社会的认识。”
上面这段话,权佳果一字一字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他内心在想,如果自己将被处死的话,这段话就是他对世人的最后遗言。
这几场审讯后,他又被扔入黑暗的牢房。每天吃两顿饭,放两次风(所谓放风,只是可以去一下小院中的厕所)。权佳果忍受着饥饿,熬完了炎夏,又得熬寒冬。这里的夏天,热得人昼夜流汗,晚间流的汗浸在床板上,以致结成一层白花花的碱一类的东西。这里的冬天,终年不见阳光,牢房里他更是寒彻肌骨。
有一段时间,作为重犯他被与死刑犯同关一室,还被戴上了约有15斤重的脚镣。
1968年12月31日,在蒲城尧山中学的大操场上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权佳果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犯”的牌子被押至会场。在宣判中,他的《认识》被称为“反革命宣言书”,被说成是“无耻地歪曲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诬蔑;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进行恶毒攻击”。最后是“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权佳果有期徒刑十五年”。
这时,台下“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的口号狂呼,震耳欲聋。
令人悲愤的是,宣判的这天,正是权佳果22周岁的生日!
沉冤难申 牢狱煎熬十一年
判刑后,权佳果被押送到秦岭脚下的莲花寺监狱,这是省劳改部门的一个开山采石、改造罪犯的石碴厂。
头天下午到莲花寺,第二天清晨他便上了工地。他所在的二中队关的全是“现行反革命”,所以干的是窝子里开采石料的又苦又累的活儿。整日在山根下劳动,山岩上松动的石块随时会滚落下来,实属危险。他们中队一个犯人,就因为一块鸡蛋大的石头砸在安全帽上,结果因脑出血而送了命。而那些非反革命的普通刑事犯,则可以在灶房、缝纫组等地方干轻松活。当犯人,政治犯也低人一等。一次,权佳果当面听见外队一个犯人不无“自豪”地说:“咱是花案!”言下之意,我不是你们这帮可怕的反革命。
这里的饭菜质量甚差,数量又不足。饥饿使他十分瘦弱,但每日却少不了沉重的劳动。抬石头若遇上个力气大的犯人,他拴的大石块把权佳果压得脊梁几乎都要炸裂。除过饥饿与沉重的劳动,这里还有许多监管制度。这里每三四个人被编为一个互监组,决不许单人行动,连上个厕都得有人陪着去。社会上有陪人吃饭的,这里则有陪人上厕所的。
在莲花寺,犯人每天要向毛主席请八遍罪。每遍请罪时,全体犯人要对着毛主席的像鞠三次躬。如此下来,每天要鞠躬24次。这里最流行的一句领袖语录是:“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权佳果默默地、艰难地抬着莲花寺石碴厂里那似乎永远也抬不完的石头。然而,在他的心中,坚信黑暗终将过去,真理和正义的光辉终将照耀祖国的大地。那时节,他不能在纸上写什么,只在心中吟成一首表达自己心志的诗:“忍将岁月付东流,豁得十年作楚囚。诚知青春秒秒贵,革命我何惜此头!”
他不能白白浪费掉这15年,他要看书,他要研究问题。但是劳改队里除过几份报纸和几本毛选外,再无任何书籍,于是他写信让家中买马列著作给他寄来。
权佳果被逮捕后,他一家人就成了反革家家属,他的父亲在批斗会上曾被人一拳打得倒在了地上。此时,他的亲人们想:佳果啊,你就是因为看马列的书,差点被杀了头的呀!你现在进了监狱,还想读马列的书,难道你真不要命了吗?因此,家中迟迟不给他寄书。他一再写信,苦苦哀求,又把监狱每月发的两元零用钱积攒起来寄回去,请求买书。他的父兄尽管顾虑重重,但出于亲情,还是给他寄来了《反杜林论》和《共产党宣言》,最后又寄来了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他细心地阅读着,思考着:中国,该向何处去?
平反之后 求索不息路漫漫
一个人的熟睡,最多不过十个小时就会苏醒;一个国家的一场昏沉沉的睡眠,竟一睡就是十年。十年的历史迷误,十年昏乱的梦!然而,人民是会觉醒过来的,党是会清醒过来的。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历史的车轮又走上了正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元月,33岁的权佳果平反出狱。
1979年8月,他作为省青联委员,去西安参加了陕西省青年联合会第五届第一次会议。1979年9月,他被政府安排为当地社办初中的民办教师,第二年春天又转为公办教师。
1984年元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成立的渭南教育学院(现合并为渭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即留校任教,现为政治经济系副教授。
由于他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优异成绩,1999年获得国家教育部主持评选的曾宪梓教育基金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二等奖(此奖项全国只有一等奖10名,二等奖50名,其余为三等奖)。他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仪式。
除认真教学外,权佳果更潜心于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他要在更深的层次上研究社会,研究人生。无论是在家乡初中教书的时期,还是在渭南高校教书的时期,他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刻苦读书与研究。在贾曲中学时,他便到西安去买书,到省图书馆去借书。到渭南后,他到西安买书的次数更频繁了。为了节省来往的车费,有时他就骑着自行车去西安买书。往返二百五十里,跑上一整天,在西安除寄存自行车花几分钱外,连一杯水也舍不得买,更不用说花钱吃饭了。他平日里不喝酒,不吸烟,生活清淡得连茶也不喝。他不打扑克,不打麻将,远离一切娱乐活动,把工作之余的一切时间,都用在读书与研究上。
迄今他已有《人生的趣与疑》、《中国伦理》、《人生大格局》、《伦理学通信》四部专著出版,另外还有多篇论文在报刊发表。
一位著名学者在他的为权佳果的《中国伦理》所写的序言里中肯地评价道:“权佳果可以说是个奇人。……奇在他心甘情愿作一名真理的探索者和殉道者,为此,饱受牢狱之难和贫寒孤独之苦,‘虽九死而犹未悔’。别人用学问、理论为自己编织花环,他却默默地用心血浇灌真理的苗圃。不管政治高压还是金钱狂潮的冲击,都改变不了他关心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情怀。”
当年的权佳果,是一名典型的志士;今日的权佳果,堪称一位深邃的哲人。集志士与哲人的品质于一身,这就是他的人格写照。
愿权佳果的理论研究成果能获得更多人的认识!
愿社会不要忘记这位不可多得的奇人!
□本报记者 杨明洲 特约记者 李高田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