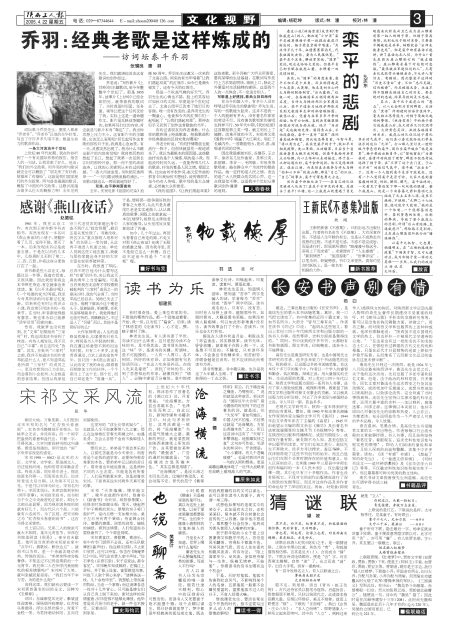
长安书声别有情
若白
最近,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长安书声》,是高信先生的第六本书话随笔集,真好,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书中收集的近四十篇文章,恰如书名所示,大部分“皆与三秦有关”。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起码从这些短文,看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文学和出版方面的一些书人书事。虽然零碎,史料方面却是靠得住的。”同时,书中谈到的许多书刊,大都附有书影和插图,图文并茂,印制精美,读来令人不能释卷。
高信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他多年来致力于书话随笔的创作,收获颇丰,已出版过多部书话随笔集。在这本仅十多万字的集子中,作者以一个学人的睿智和勤奋,钩沉辑散,辩难正误,用大量翔实的史料,生动流丽的笔墨,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陕西文学和出版方面的一系列书人书事,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挖掘、梳理和考辨,既彰显了陕西文学和出版界对新文化事业的贡献,又以极具说服力的分析论辩,纠正了许多讹误与牵强附会之说,令人耳目一新,获益多多。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陕西一直未得到研究者的应有重视。譬如,像1940年初由著名湘籍女作家谢冰莹主编的文学月刊《黄河》,1944年由文学青年彭古丁主编的《高原》,1945年由赵望云主编的图文杂志《雍华》及由著名书法家寇遐题签的文摘月刊《书报精华》等等,在陕西的出版和传播情况,或因刊期较少,或因发行量有限,就长期不为人知,甚至包括文学出版界的读者,对它们也知之甚少。高信先生不弃微末,经多方寻访搜求,查证考辨,不仅详细再现了这些书刊创刊的始末,而且凸显出它们在那个非常时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给人以深刻启示。尤其像1949年三原县中学师生创作和编印的一本《人民木刻》,仅出版过薄薄一期,其中也只有三十多幅作品,作者也没有轻视它。不仅对它的创作出版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掘考证,而且对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再如,对知堂(即周作人)旅陕佚文的钩沉,对陕西新文学运动先驱人物郑伯奇先生著作长期湮没不受重视的呼吁,对《商州山歌》手抄本的发掘研究等等,都可以见出他在钩沉辑散方面,涉猎之广,用功之勤。而对陕西文学和出版界的上述种种成就,他深有感触地说:“陕西虽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热土,但也并非一片被现代文学遗弃的白地。”“在这里也有过一批知名的不知名的志士仁人,在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代文化传统和根基,只是在近代才日显颓势的地面上耕耘守护着开拓着,从而维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脉在这里未曾中断”。
鲁迅先生只到过一次陕西,就是1924年七八月间应邀来陕西讲学。鲁迅先生去世之后,关于他的这次活动,先后出版了多部专著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政治的种种原因,许多著作、回忆文章对鲁迅先生这次西安之行及其活动情况,或添枝加叶任意演义,或想当然地加以拔高附会,以致谬论流传,完全背离了当时事情真相。高信先生坚持以实事求量的科学态度,运用大量丰富的史料一一加以辨析,廓清迷雾,纠谬正源,还事情以本来面目。他并不因自己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和热爱,人云亦云,为尊者讳。充分说明他作为一个严肃学人可贵的学术品格,令人钦佩。
语言温润,笔墨含情,是高信先生书话随笔文章的又一突出特色。作者每每以行云流水般的文章叙事抒情,书人书事,而且始终坚持“着笔往昔,着眼现在,追求史料性知识性与现实性的联婚”,即给人们阅读的愉悦和享受,又给人深刻的启迪和警醒。该集子中许多篇章,诸如:《读“有感”有感》、《想起了郑伯奇先生》、《一卷遗文倍有情》、《何时共论文——追怀钟朋教授》及《京华访学六日记》等等,不仅融史料性知识性和现实性于一炉,而且篇篇都可称为优美的散文佳构。
现代书话文章因唐弢先生而滥觞,高信先生可谓学得书话三昧者也。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