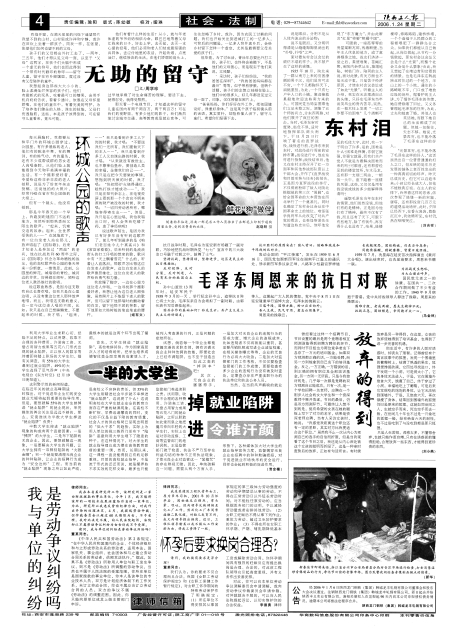
本版导读
东村泪
说是眼泪,分明不是从人体内流出的分泌物;
说不是眼泪,又分明听得清是从缝缝隙隙里淌出的“扑嗒,扑嗒”之声。
面对着东村会议会址的破烂不堪的样子,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感慨。
1935年10月,陕北来了一群从南方上来的穷困潦倒的男子汉,他们虽穷可志不穷,一个个又都胸怀天下,肩挑重担。为此,一个只有七户半人口的小镇,像迎接救星般地欢迎这些南方来的人。可国民党当局妄图乘他们立足未稳之际,调集了五个师的兵力,分东西两路,对他们展开了疯狂的围击。当时,毛泽东审时度势,临危不惧,适时地指挥部队调头南下,于11月21日打响了著名的直罗战役。战役进行前,毛泽东来到东村,对战役进行周密的安排布署;战役进行中,他在东村进行指挥;战役结束后,他又在东村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和其他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大会,并作了《直罗战役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正是因为直罗战役的举行,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也给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同时也确定了东村会议会址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难怪张学良将军从此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也难怪斯诺先生知道这些史实后,惊呼他发现了“东方魔力”,并由此断言“红星”将要“照耀中国”。
可眼前,一座孤零零的房屋梁断瓦碎,残墙断壁,当年主人休息的地方,成了禽兽栖身之地,战友们济济一堂之后,粪便堆集,苍蝇汇聚。而院内杂草丛生,墙塌地陷,树枯门冷。陪同的主人说,面对此景,有关方面也不是无动于衷,只是苦于经济原因,才使东村会议会址成了如此“光景”。听着主人的介绍,我实在无法理清自己的头绪,只好在毛泽东当年谈笑风生的房内苦寻。突然,在一根木柱上发现“一切工作要不怕困难”几个清晰可见的毛体大字。此时,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是的,困难是什么?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而我们共产党人不就是为着解决困难而来的吗?可眼前,还有那曾经见到的楼堂馆所,车水马龙,还有那一支烟二两油,一顿饭一头牛,座下跑着一座楼的风景。这些,又仅仅是用有钱没钱或钱的多少能解释得清吗?
遥想毛泽东当年在东村的情景,他们虽然没钱,但他们有的是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有了精神,最终不仅有了钱,而且还有了天下,可眼下有些地方,除了有钱外,再穷得什么也没有了。结果,修楼楼垮,修路路陷,建桥桥塌,一个个造福于人民群众的工程都喂肥了一群群乌合之众。如果我们都能从自己做起,从岗位做起,从节约一分钱做起,那东村会议会址又会是什么“光景”,而整个社会又会是什么景象?由此,我又想起了在靖边青阳岔看到的情景。也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住过的一个地方。半山上的一个小院,通往的小路崎岖不平,门口成了堆放垃圾的场所。据看护的主人讲,为了缅怀毛泽东的伟绩,她自费修缮了旧址,又义务管理起毛泽东的住所。为此,丈夫和她离了婚,其他人也笑话她,而眼下她自己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但她一如继往,矢志不移。她说,光景再穷,也不能冷落了毛泽东这样的好人。
“光景再穷,也不能冷落了毛泽东这样的好人。”这话虽然出自一位普普通通的妇人之口,但反映的是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上老百姓发出的一种真真切切的呼声。昨天已成历史,但它可以启迪未来;小孩已经长成大人,但他不能数典忘祖。在主人的安排下,我带着这样的思索,依次参观了修缮一新的宋窟、唐塔,还有那投资几百万元的道观活动场所。此时,夕阳已经西下,在香火袅袅,暮鼓沉沉中,我依稀听见,东村仍然在咽咽哭泣。
(刘吉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