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行记
[香港]杨树培
从嘉峪关驱车前往敦煌约五个小时的行程,除经过玉门镇和安西市时有一小段绿洲从眼前掠过外,所见的都是戈壁。已是九月,刺目的骄阳仍烤灼得车里的人燥热难耐,携带的饮料很快就喝完了,嘴唇开始起皮。晴空中忽有一道电光从天而降,一闪,便又在戈壁滩上无痕无踪了,我惊诧还真有“晴天霹雳”呀!偶然间又见远处似有村落和树影,司机说那是“蜃楼”,道路稍一偏转那虚幻的景象便消失了。
我迷茫地望着车窗外,稀疏的骆驼刺草星星点点地洒落在石滩上,延伸到天际便成了一片灰色。一只金雕在空中悠悠地盘旋,懒洋洋地落到石滩上,耸起金黄色的翅肩。热浪不时卷起旋风,夹裹着沙石像白日的幽灵在石滩里游弋。远方的祁连山延绵百里,却见不到一棵树,只有雪线以上的峰巅泛着微微的银光。这就是戈壁,不身临其境是无法真切地体验荒漠的苍凉的。
终于,我们看见了前方有一片绿洲。汽车开进了胡杨树林掩映下的一座石牌坊,那牌坊上有一匾,匾上有三个大字——莫高窟。我的心跳开始加快,朝思暮想的圣地到了。一进牌坊,眼前的景象与刚刚几个钟头在荒漠中的所见相比,反差太大太突然,只见偌大的水泥停车场上停满的各式轿车足有上百辆,熙来攘往的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游人,密密麻麻,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我急着想见到莫高窟,但浓密的钻天杨树和连片的旅游商店遮住了视线。
莫高窟区的美丽和豪华大大超出我的想象。
我们走过河床上的一座大桥,立刻被浓阴所覆盖,高大的胡杨林遮天蔽日,林间花团锦簇,整洁的水泥路两边浇花的喷头纵情地喷洒着甘露般的水雾,置身其间,已全然不察身外的天旱地荒。大约在林阴道中走了约半里路,我们看到了石窟的外壁,沙山下,横亘千米的峭壁被整个儿用混凝土构筑的厚实框架如巨网一样牢牢罩住,每一个“网眼”里都有一扇或几扇铝合金做成的百页门,门楣上都有编号。莫高窟现在492扇这样的门,每一扇门里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宝窟。这些窟门的两侧都用混凝土浇铸了宽厚的护墙,粗砂墙面看起来像花岗岩壁一般坚实挺括。有些窟门的上方还存留着各个朝代建筑的风格不同的窟檐,有些窟檐下还残留着外壁上的彩绘,这些窟檐和彩绘都被精心地加固了。整个窟区气派堂皇而又气势雄阔。我走近唐代建筑的九重塔楼,这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肃立在楼前的广场上,仰望层层飞檐,一种膜拜顶礼的祟敬之情强烈地撞击着心扉,不觉之间眼眶都湿润了。
为我们打开的第一个窟是南头的105窟(盛唐)。我们揿亮手电,在门后东壁上一眼就认出了熟悉的《维摩诘经变》。壁画中的维摩诘是一位居士,精研佛学,他病后,文殊菩萨来看望他,两人谈论佛学引起激烈的辩论,维摩诘精彩的雄辩把众神都折服了,天女听得入神,手捧的香花从空中散落也未察觉(天花乱坠),众罗汉流露出惊愕的表情,人间的帝王也在专注地听讲,他的群臣恭顺地拥立在他的身边。画面上的维摩诘坐在高脚胡床上,身体微向前倾,表情激动而沉着。作者用流畅刚健的线描在白壁上,一气勾成,再施以淡彩,造型准确生动,可谓形神兼备。这是唐代壁画中描绘维摩诘形象的一幅杰作。
我们一共走进了三十多个窟,有北朝到隋、唐、西夏、元各朝的洞窟,其中以唐代的洞窟最多,内容也最丰富。我们认真阅读每一幅壁画的内容,啧啧赞叹那些惟妙惟肖的塑造技艺。我们感受着石窟艺术整体的灿烂恢宏,同时又用心捕捉并体味精微之处的堂奥。整整一天下来,我们一个个从颈脖到脚根都痛得不能自持,但大家依然兴致勃勃。
窟区北侧一个硕大的洞窟(现编为第16窟)甬道的北墙内,暗藏有一“影窟”。1900年6月,当时看守下寺的一个王道士在清理该窟的积沙时无意间发现了它。从这个窟中出土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批惊世文献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洞内还供奉着晚唐时期的高僧洪巩的泥塑写真像。造型极为传神,虽历经了1100多年,仍保存完好,栩栩如生。塑像背后绘有壁画,其右侧是一侍女像,画风简洁写实,形象丰润可人,近代大师张大千曾临摹此画多处被发表,我们很熟悉,现在看到原作,倍感亲切。
在敦煌研究所的陈列馆,我们观摩了一批特级窟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完全是按照原窟原物大小、形态、造型、设色以及塑绘的程序一模一样的“克隆”出来的,甚至连残缺和剥落的斑痕也精微到乱真的地步。据介绍,复制一个窟需要十几位专家日复一日地连续工作一年才能完成,可见工作量之大和辛劳的程度。这样做既满足了让更多的人参观研究特级窟的需求,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最珍贵的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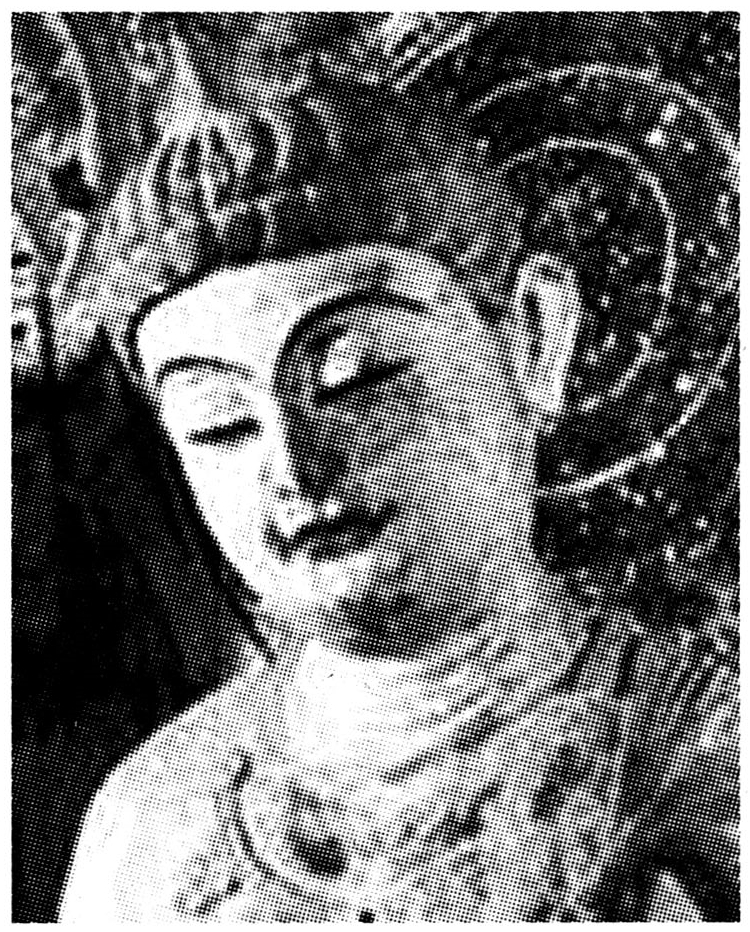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