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阀”朱维铮
历史学家朱维铮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贡献突出,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2006年,德国汉堡大学授予朱维铮荣誉博士称号,并称赞他是“低调的大师”,国内学术界则称朱维铮是“中国最后的经学家”。朱维铮在备受称赞的同时也颇遭非议。不少人将他视为是中国学术界的另类,有人甚至称他是“学阀”。
作为历史学家朱维铮不跟风,敢直言,不随流俗,不人云亦云,始终坚持史家的史实和良知。对待历史,他总是强调认真,“用历史去说明历史,先考虑是什么,再去问为什么”。他常说,一名历史学家若能在一个领域留下三句话让后人永远记住,那就很了不起。2010年12月15日,朱维铮在给复旦大学本科生上的最后一课上说:“讲到历史问题,如果你乱说,我就要说你乱说,我可不管你是谁”。直到去世前他还感慨:“讲真话很难。你说的话到底合不合历史?到底会不会被历史承认?到底会不会被历史否认?”正是因为出于这种对历史的较真态度,朱维铮常常不留情面地指出别人做历史研究时的错误。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批评于丹对《论语》缺乏基本常识,连文本都不懂。即便是对他最敬重的马一浮、陈寅恪等大师级人物也不例外。朱维铮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回忆,从他刚入复旦起,朱维铮就不断告诫学生要扎扎实实做学问,“很多人自以为聪明,判断力很强,就望文生义、跳过很多考证的程序,看似走了捷径,却压根不是在做学问”。李天纲说,朱维铮特别反对因为权势、外部利益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被意识形态和政治风气所左右。他始终想警醒学术界,要把政治和学术分开,不能曲学阿世,这来自于他对自己一代人经验的深刻反思。质疑、解惑、求真,这是朱维铮治学的目标也是他治学的境界,学问做到这一步,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对于当今的学术生态而言,朱维铮很多时候的确称得上是特立独行。他脾气坏,桀骜不驯,好骂人,盛气凌人,遇有不合意的,立即开骂。一次,他对王元化说:“你当上海宣传部长三年,一事无成。”还有一次他和刘志琴见面,劈头一句:“你怎么去抢文学家的饭碗,一个历史还不够你搞的!”对于好骂人,朱维铮自己的解释是“有人说我喜欢骂人,但什么是骂人?我实事求是地说事实,怎么叫骂人?”“我赞同鲁迅的话,批评就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朱维铮动辄就骂人,因此很多学术会议不敢请他参加,怕他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更有甚者:他将自己所带学生的作业改掉三分之二,从不手软,也不护短;他讨厌一些学者没有创见而偏要去写长篇大论的“学术专著”;他厌恶现行的学术条框和学术语言;他不大愿意申请课题并曾经在课题有何作用一栏大笔一挥,写上“无用”两字!他感叹“假大师满天飞”,他说,“大师,当以时间做裁判”。对于海外学者赞誉他为“低调的大师”,他谦称自己是“一名中国历史研究的从业者”,在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说自己只想充当一名“读者”。他说:“我能做到的只有一条:管好自己。教师是我的职业,我只能要求自己遵守应有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
朱维铮之所以被一些人视为是学界的“异数”,完全是因为在一个要求统一、思想一律、抹杀个性的环境下,人们早已习惯于既定的规范和事实,习惯于墨守成规,凡有出格者都视为异类,甚至加以排斥。但是平心而论,对于当下的学界来说,缺乏的恰恰是朱维铮这样的有学问的思想家、有思想的学问家,有棱有角的迷人的“学阀”。
□史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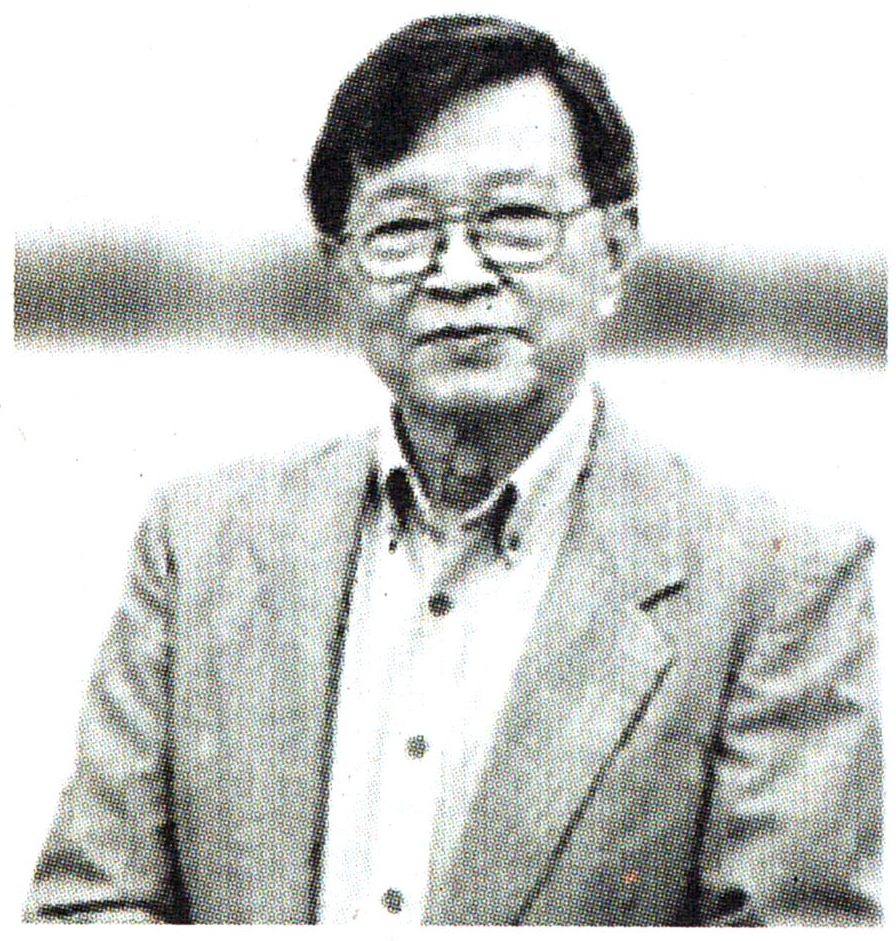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