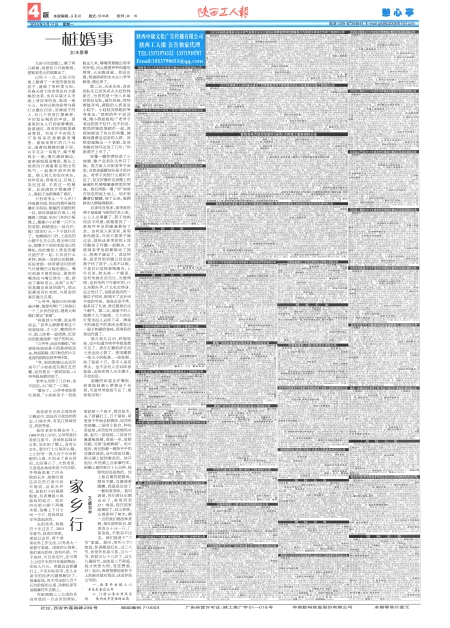一桩婚事
文/王思琴
大房子的屋檐上,落了两只麻雀,刚要张口开始歌唱,便被老李头的烟熏走了。
已经十一点,大院子的地上摆满了一米宽的银色铝盆子,盛满了各种菜与肉。有春天刚下的青菜还有才暖熟的韭菜,也有早晨才从市场上背回来的鱼,堆成一座小山。各种式样的彩带与喜灯点缀在四面,而满屋子的人,有几个邻里打着麻将,不时发出喝彩的声音。里屋里的女人们则抿着嘴唇,脸蛋通红,弯弯的眉眼里满是喜悦。有孩子不时把大厅里得来的喜糖塞进嘴里。被唤来帮忙的几个壮汉,端着热腾腾的臊子面,右手叉开一双筷子,辣子醋挥手一倒,嘴巴凑到碗边,面条便吸溜进嘴里,鼻头上细密的汗滴随着这喷出的热气,一起散在清冷的夜里。猫儿狗儿的也在欢乐,结伴而来,穿墙而过,在地上来回巡视,不放过一粒粮食。此刻满院子都塞满了人,满院子也都填满了喜庆。
只有老李头一个人在门外吸着旱烟,细长的烟杆被他擒在手指里,粗糙的手腕轻轻一抖,烟灰被磕到石堆上,他翘着二郎腿,坐在门外的小板凳上,瘦瘦小小好像一只不大的老猫,眼睛透出一丝光芒,被门里的灯火一下子就扑灭了。他蜷缩在门外,土蓝色的小帽子扎在头顶,冒出两只耳朵,那帽子下面的毛发也已经稀松,他的整张土黄色的瘦长脸拧在一起,五官没什么奇特,倒是一双狭长的眼睛,好似老猫一样带着诘问的语气代替嘴巴从眼角溜出。嘴巴和鼻子靠的很近,深深的嘴角纹与嘴巴堆在一起,挤成了秦岭老山,此刻“山沟”里是飘出淡淡的烟气,他云里雾里吞吐老烟,与里面的喜庆毫无瓜葛。
“山爷爷,俺妈叫你给俺破开糖,俺要吃啊!”门里跑出一个三岁多的娃娃,瞪着大眼睛盯着这“老猫”。
“碎崽娃少吃糖,进去咥面去。”老李头静静看着这个碎崽娃娃,才三岁,嘴甜的不行,脸上挂着一道清鼻,红彤彤的脸蛋透着一股子的机灵。
“山爷爷,面没有糖甜。”碎崽娃娃抽抽鼻子把鼻涕吸进去,眯起眼睛,张开粉色的小手直直的顺势坐到爷爷怀里。
“爷,姐姐她嫁出去还回来不?”小娃娃把玩着红红的糖,没有看见一提到姐姐,山爷爷脸色瞬间变了。
老李头呆愣了几分钟,也不说话,大口吸了一口烟。
“熏死了。山爷爷老妖怪吐黑烟。”小娃娃身子一低就躲出几米,嘻嘻笑着跑出老李的怀抱,回头看看爷爷佝偻的脊背,大步跑进屋。他没注意,两滴清清的水水从山爷爷眼里,溜出来了。
第二天,天还未亮,迎亲的队伍已经风风火火赶到韩家庄,为首的是十里八乡最好的仪仗队,披红挂绿,唢呐锣鼓齐鸣,满眼的人挤进这小院子。小娃娃突然跑到爷爷身边:“那男的咋不说话哩,俺小燕姐姐呢?”老爷子老远把孩子拉开,也不回话,眼角的皱纹堆砌在一起,深深地嵌进了灰白的两鬓,缄默地看着这迎亲的人群。突然里屋跑出一个老娘,急匆匆躲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你家燕子上吊了。”
好像一颗炸弹扔进了小池塘,整个迎亲队伍炸开了锅。男方家人冲到老爷子面前,自家亲戚瞬间往屋子里冲去。老爷子突然什么都听不见了,但又好像听见房檐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像秦腔里的哭丧。然后两眼一懵,“砰”地倒在灰色的泥土地上。他手里攥着红糖糖,掉了出来,被拥挤的人群踩得粉碎。
后来传言很多,那李家的燕子是准备飞到同村某人家,心上人出事瘫了,燕子他妈死活不同意,就随便找了一家条件齐全的硬逼着结了亲。也有说人家亲家,家里条件殷实,许诺只要燕子嫁过去,就给这老李家把土地问题房子问题一起解决,才使得老李他那婆娘动了狠心,把燕子逼去了。说法特多,甚至传到邻镇已经变成燕子怀了孩子,人却不认账,于是自己觉得羞愧难当,上吊自杀,给夫家一个颜面。也有传她贞洁无比,为爱殉情,也有传的下作难听的,什么未婚先孕,什么私定终身。总之传开了,也就是饭间的一顿瓜子时间,影响不了这乡间不变的平淡。喜丧本是平常,最多还了礼钱,谁还愿意沾这个晦气。第二天,满屋子的人就剩下几个妯娌。大大的红灯笼也没人去卸下来。满屋子的满盆子的菜肉全都发出一股子刺鼻的臭味,那堆积的鱼也死透了。
很久很久以后,碎崽娃娃,也不知道为啥爷爷姐姐都不见了。那红红糖纸碎在泥土里也没人管了。那里藏着一张小小的纸条,一张收据,收了张家十万。签字人是老李头。也不会有人告诉碎崽娃娃,这张家男人天生傻子,不会说话。
那糖的味道含在嘴里,碎崽娃娃满心梦着这个东西,可是爷爷姐姐不见了,谁给他买呢?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