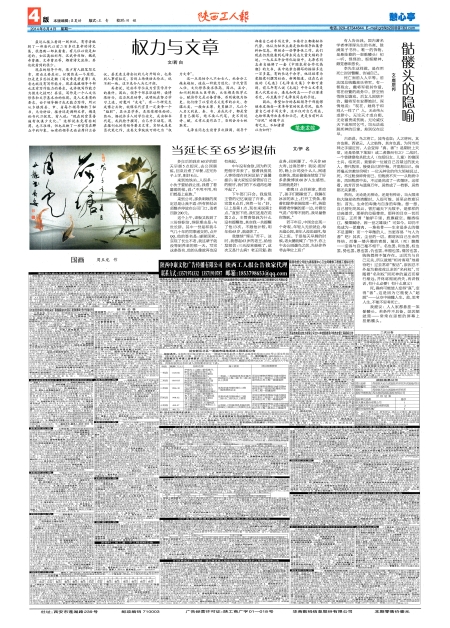骷髅头的隐喻
文/鹿居邦
有人告诉我,国内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的书斋,除满架子书外,唯一的饰物,是悬挂着的一架骷髅头!初一听,怪怪的,细细默神,颇觉意味悠长。
李先生这样做,是在用死亡时时警醒、告诫自己。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前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有一智残女,戴将军极其怜爱,常在纷繁的政务中,挤空悄悄陪女嬉戏。后女儿因病不治,戴将军在安葬她时,深情地说:“现在,她终于和别人一样了!”人,无论伟大或渺小,无论天才或白痴,无论富贵或贫贱,无论威仪天下或形同乞丐,均无法逃脱死神的巨掌。差别仅在迟早。
古语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西谚云,人之临终,其言也真。为何当死神之手逼近时,人会变得“真、善”?是期盼上天堂,还是恐惧下地狱?或二者兼而有之?二战时,一个曾肆意枪杀犹太人(包括妇女、儿童)的德国士兵,临死前,竟要求一位被自己囚禁过的犹太人,替代牧师,接受自己的忏悔,并宽恕自己。倘若毫无宗教信仰呢?一位无神论的伟大领袖说过,死,不过粉身碎骨而已,但物质不灭——从物质中来,再回物质中去,不过是完成了一次循环。这样看,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居然成了一档事,居然都无关紧要。
然而,无论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当大限来临大脑却依然清醒时,人很可能、甚至必然意识到:首先,生命的卑微与自身的卑微。想一想,自己曾叱咤风云,曾打遍天下无敌手,是那样的功高盖世,那样的位极尊荣,那样的目空一切而狂妄,正所谓“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哉!”可如今,却仍不免成为一团腐肉、一堆枯骨——生命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而一个卑微的人,当更容易“与人为善”吧?其次,尘世的一切,都将因自己生命的终结,而像一缕升腾的青烟,随风(死)飘散——变得与自己毫不相干。名也罢,利也罢,权也罢,势也罢,恩也罢,仇也罢,幸福也罢,痛苦也罢,统统都将不复存在。正因为与自己无关,所以就能“相对客观”地看待吧?过去常讲“假话”,原因总不外是为着孜孜以求的“名利权”,可随着“名利权”因死神的逼近而渐行渐远,并终将彻底消失,再讲假话,有什么必要?有什么意义?
死,确有可能使人变得“真”,变得“善”,这是因为它能使人“超脱”——从空中俯瞰人生。故,思考人生,不能不思考死亡。
我提议:人人家都悬挂一架骷髅头。若条件不具备,就因陋就简——常常在思想的屏幕上挂骷髅头。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