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遮蔽的大师
——论汪曾祺的价值
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地色盲。有一个作家去世十八年了,他的名字反复被读者提起,他的作品反复被重版,年年在重版,甚至比他在世的时候,出版的量还要大,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师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冷淡了他,雪藏了他。
他就是汪曾祺。
翻开当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
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纵观这些年被热捧的作家常常是踩到“点”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围观。那么这个“点”是什么,“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中国文学的“点”,大约由两个纵横价值标杆构成。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在1978年前这个外来标准,是由前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稍带一点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而1978年以后的外来标准则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而汪曾祺的作品,则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先说革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在鲁迅时代已经形成,这就是“遵命文学”,鲁迅在《呐喊》的自序里明确提出要遵命,遵先驱的命。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思潮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汪曾祺的创作自然无法配合这些重大的文学思潮,因而就有了“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的感慨。“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正好说明汪曾祺在文坛被低估的原因。苏北在《汪曾祺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记述了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一段往事: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程鹰说:“是的。”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汪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林用发亮的眼睛望着汪,笑了。
汪说:“我的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
这也是目前的文学史对汪曾祺的评价过低的第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以革命的价值多寡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上不了头条”的汪曾祺自然就难以占据文学史的重要位置,汪曾祺很容易被划入到休闲淡泊的范畴,容易和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为伍,只能作为文学的二流。
1978年新时期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热潮为何又将汪曾祺至于边缘呢?
这要从汪曾祺的美学趣味说起。汪曾祺无疑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巨大影响,但汪曾祺心仪的作家正好是国内现代主义热潮中不受追捧的阿索林。而阿索林在中国的影响,就远远不能和那些现代主义的明星相比了。很多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也不见得了解多少,至今关于他的论文和随笔译成中文的也就20篇左右。
汪曾祺游离于上述两种文学价值体系之外,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点”上,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今他在读者和作家的慢热,持久的热,正说明文坛在慢慢消褪浮躁,夸张的现出原形,扭曲的回归常态,被遮蔽的放出光芒。当中国文学回归理性,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汪曾祺开始释放出迷人而不灼热的光芒来。
汪曾祺的价值在于用他的作品激活了传统文学在今天的生命力,唤起人们对汉语言文字的美感。早在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风起云涌的时候,他在各种场合就反复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当时看来好像有点不合时宜,而现在看来却是至理名言,说出了中国文学的正确路径。汪曾祺通过他的创作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汉语美感,激发了那些隐藏在唐诗、宋词、元曲之间的现代语词的光辉,证明了中华美文在白话文时代同样可以熠熠生辉。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传承渗透在汪曾祺作品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触角在小说散文之余遍及戏剧、书画、美食、佛学、民歌、考据等诸多领域,他的国学造诣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读者。
汪曾祺的价值还在于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将知识分子精神、文人传统、民间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由于五四作家大多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他们的作品虽然都是拿来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存在着过于浓重的文人创作痕迹,不接地气。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也带着这样的痕迹。而建国之后的小说,则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小说文气依旧,但接地气,通民间,浑然天成。建国后的文艺政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绳,讲话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文艺家要向民间学习,向人民学习。这让汪曾祺和同时代的作家必须放下文人的身段,从民间汲取养分,改变文风。而汪曾祺得天独厚之处,他和著名农民作家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五年,赵树理是当时文学界的一面旗帜,又是汪曾祺的领导(赵树理是主编,汪曾祺是编辑部主任),汪曾祺很自然会受到赵树理的影响,汪曾祺后来曾著文回忆过赵对他的影响。而《说说唱唱》具体的编辑工作,又让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据说有上万篇。时代的风气,同事的影响,阅读的熏陶,加之汪曾祺天生的民间情怀(早年的《异秉》就是市井民间的写照),让他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而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张家口乡村之后,更加体尝到民间文化的无穷魅力。
他的一些小说章节改写于民间故事,而在语言、结构的方面处处体现出民间文化的巨大影响。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对汪曾祺所呈现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点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也许汪曾祺的“民间性”不如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鲜明,但汪曾祺身上那种传统文化的底蕴是山药蛋派作家难以想象和企及的,雅俗文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在这方面,汪曾祺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第一人。
汪曾祺可以当之无愧称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他的“大”在于融汇古今、贯彻中西,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他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瑰宝,随着人们对他的认识深入,其价值越来越弥足珍贵,其光泽将会被时间磨洗得越发明亮迷人。 □王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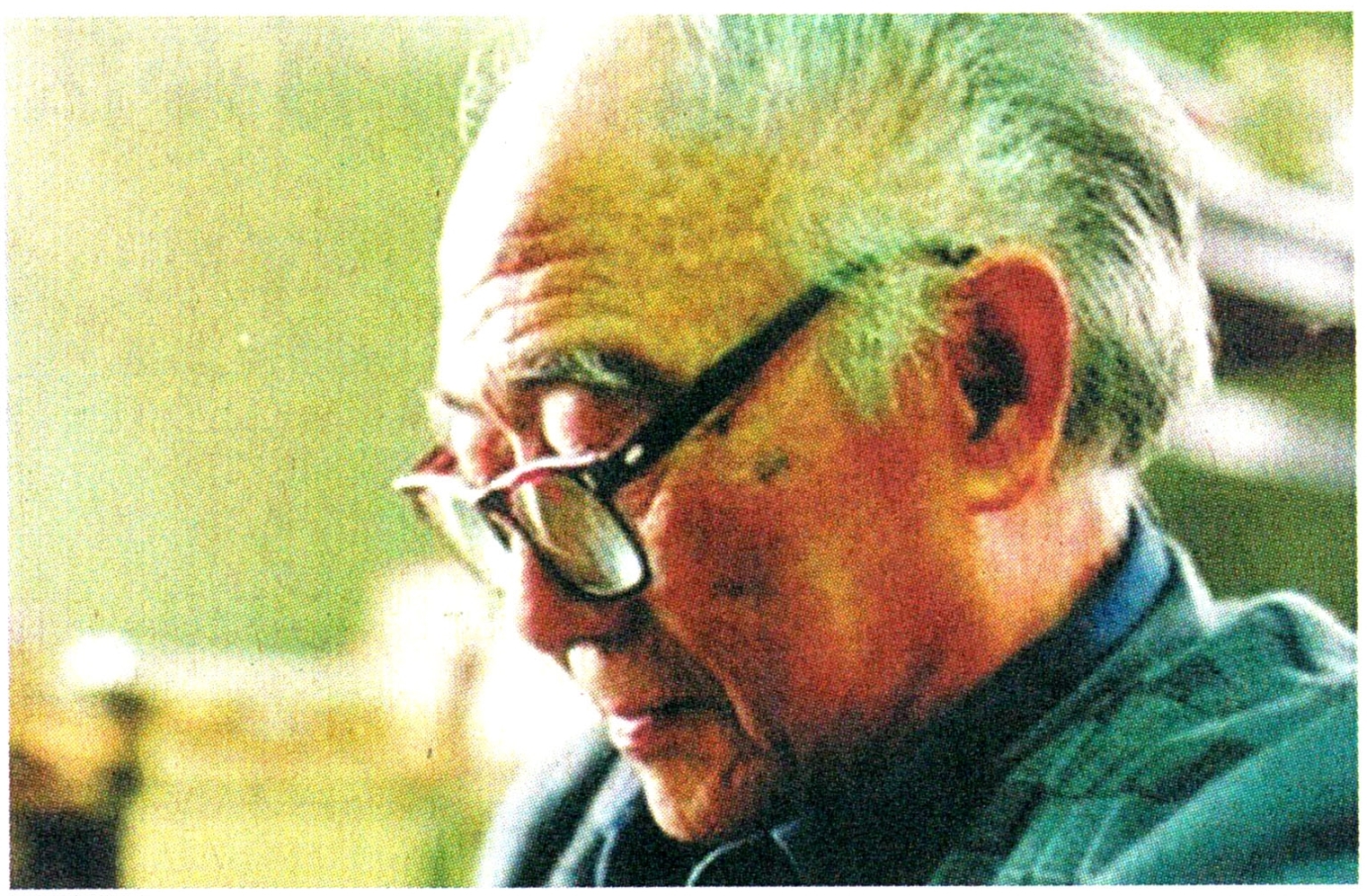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