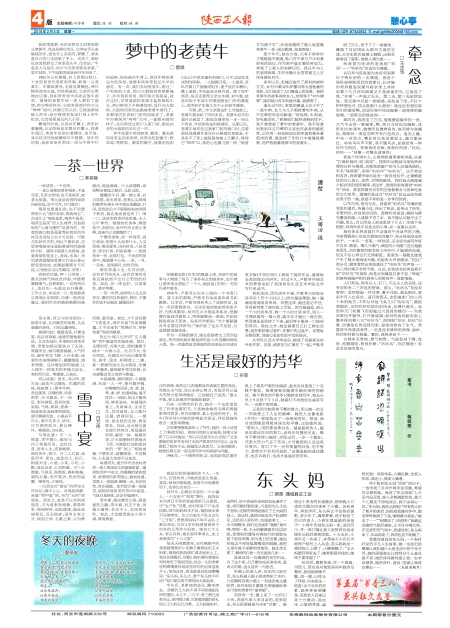东头妈
□郝英 蒲城县总工会
她是位普普通通的乡下人,一生平凡,历经坎坷,可她却是那么坚强、宽容,每每回想起她,我便不由地潸然泪下,往事历历在目……
1975年,在渭北平原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女孩子“呱呱”降生。我的到来为昔日平和的家庭增添几分喜悦,可“生产队”时期,农村家家户户生活拮据,因为妈妈奶水不足,饿得我半夜不住地啼哭。加上后来生产队又实行“工分制”,爸爸和妈妈不得不去队上参加劳动,年仅4岁的我便被寄养于村东的王秀玲大妈家。她有七个儿女,老头有病,她在家侍奉老头,加上我便成为“十口之家”。
每天天刚蒙蒙亮,还在熟睡中的我便被爸爸用小花褥子裹着送到王大妈家,爸爸和妈妈便忙着去地里上工。我总在睡醒后,仰着小脸听着听着便乐呵呵地吃下碗里的饭,炕边一头的老爹也咧着嘴慈祥地说些好听的话来逗我开心;每每这时,我也备受启发地嘟囔说:“东头妈,东头大,要个东头娃不听话!”他们便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半年后,老爹病情恶化,撒手西去。悲痛的王大妈不得不再次挑起生活的重担,大儿子,二儿子,老三都已成家另过,老四刚订婚,可那笔厚重的财礼钱让王大妈无比为难。王大妈跑东村,走西村,好不容易在亲朋好友处凑齐了钱,将四媳妇娶到家,可是因为儿子也不宽裕,还账的事情就落在了王大妈的身上。就这样,她抽空就去生产队剥棉花,还给别人家织布、纺线做零工。一天半夜醒来,我听见纺线车“嗡嗡”地作响,睁眼一看,王大妈蜷着腿在炕边纺线,那微驼的腰身在煤油灯的昏暗光线下更显单薄,因为连日的劳累,她边纺线边不停地揉着酸涩的眼睛,我把头埋在被子里静悄悄地哭。她太苦太累了,鬓角的白发一天天更添几多……
就是这样一位瘦弱的农村妇女,为了这个家,自己哪怕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难,也从没有一句怨言。
听镇上的老人讲,早年四川闹灾荒,东头妈被人贩子拐卖带到了关中,几经辗转后被小镇上一有钱的地主婆收养,再后来地主婆做主将她嫁给老实可靠的老爹作“童养媳”。
突然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位四川小伙,说是代家人来寻亲的,说来说去,东头妈便被视为寻亲“对象”。她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按照线人口述的大概方向来到了小镇。见到青年,再加详问,东头妈止不住热泪盈眶,多少年了,魂牵梦萦,终于盼到了自己的亲人,小青年竟是她的亲侄子!小青年告别东头妈一家,返回四川,并一再叮嘱让家人安排好后再来接东头妈回老家团圆。十五天后,小青年又一次来了,并带来不少四川当地特产给村上人品尝,东头妈收拾一番和侄儿上路了,小镇沸腾了:“王大妈要回老家去了,她老家挺有钱的,她终于要享福了!”
10天后,噩耗传来,在一个清晨,当侄儿、侄女高兴地到房间叫她用早餐时,发现她深睡不醒,再一摸,已停止了呼吸,叫来医生一检查:由于长年的劳累,她各种疾病缠身,见到亲人后连日来十分激动,高血压、心脏病并发,溘然长逝!消息传来,小镇沉默,全家人伤悲,我还小,被家人瞒着。
终于盼到东头妈“回家”的日子,一放学我三步并作两步往回跑,希望早点看到她。我进了东头妈家门,只见内设灵堂,家人全都满脸忧伤,那几个儿媳还不停地哭泣,我不由得心一沉,“东头妈,我东头妈呢?”所有的人听了都开始流泪,妈妈把我搂在怀中,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哽咽着对我说:“她去了……”“到哪去了,快说呀!”我被这悲痛的气氛所感染,止不住号啕大哭。在这悲伤的气氛中,我感觉到,东头妈走了,永远地走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慈祥善良的东头妈,一个农村妇女的平凡人生故事,她一生经历的磨难让我知道什么是生活中的千辛万苦,她的顽强意志让我明白什么是自强不息,她的谆谆教导更让我一生学会感恩,她的淳朴、善良、坚强让我终生难忘…… (本报有删节)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