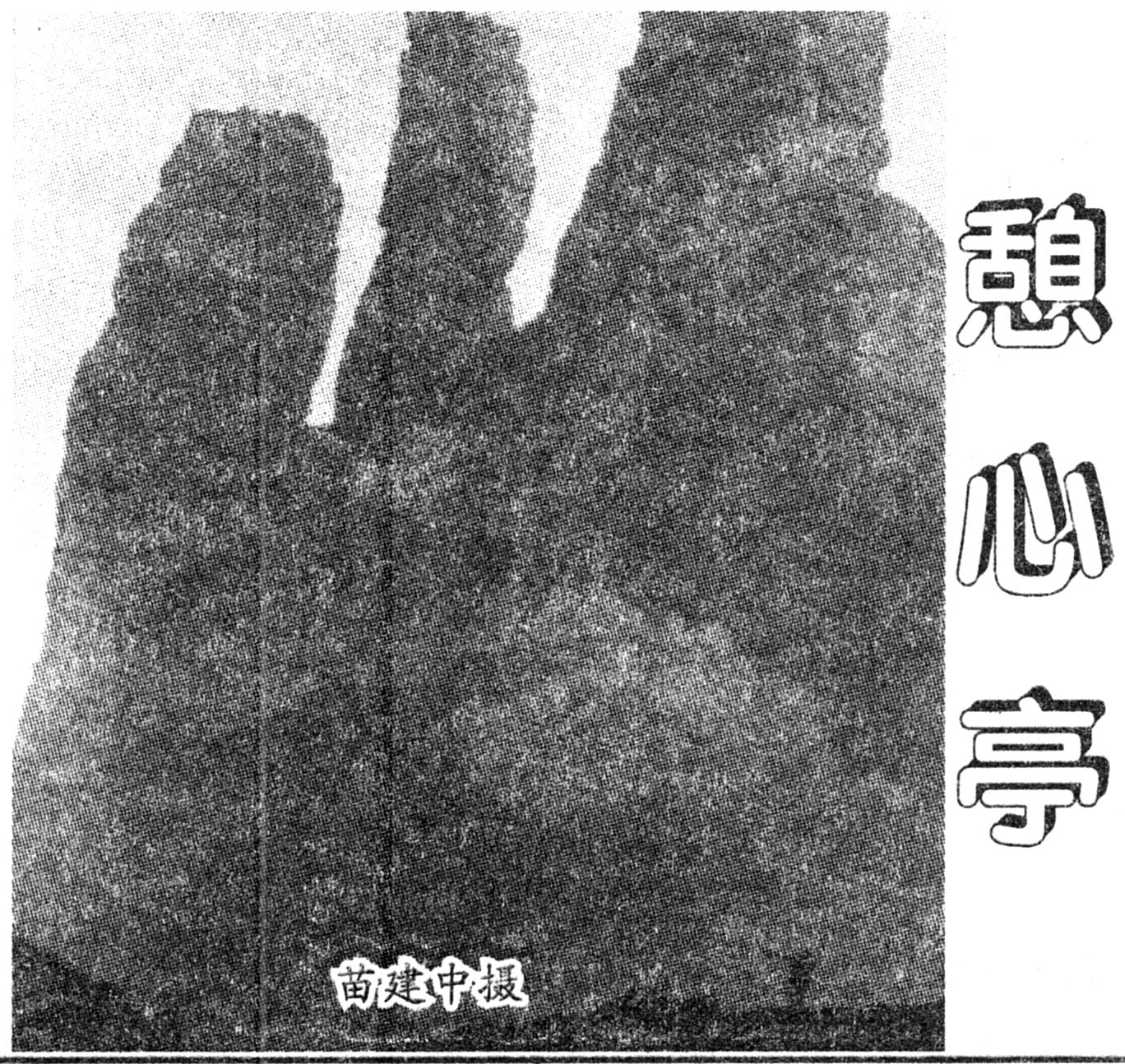文/赵彦冰
天气一天冷比一天,寒冷的风中不再有枯叶飞扬,偶而随风飘落落于山尖的白雪报知人们冬天的到来。矿山的路上行人更少,一功归于寂静,似乎今年的冬早早到达了这个偏远的矿区。
运矿的车辆来来往往,却无法缩短城市和矿区的距离。空寂是矿山永恒的旋律,生活总不方便。就如这双底子开裂的棉鞋,只要补补就会又合脚又暖和,在城里边这个事根本不用操心,随便一个街旮旯都会有补鞋摊子。可是现在,唉
夜里又飘起小雪,早晨天气又冷了许多。“下雪不冷,化雪冷”,“看来今天又要挨冻了”,年初和我同时来这儿工作的小王搓着手看山高处的积雪,一边跺着脚说,“我的旧冬鞋得修理修理。”
路道太滑,看来两、三天内不会有车来往了,大家都只好盼天晴。天晴了回家带上冬天的衣物,或补补破了的鞋子。
“看,他是干什么的?”中午饭后,大伙都缩在自个的房子,小王对我指指院子的一角,那儿有个人。一个老人,不,是个中年人。他头发杂乱,满脸挂着冻僵的皱纹,的确难以估计他的真实年龄。衣服脏旧单薄,衣服和他那双已被泥水打湿的黄胶鞋一样,补着许多像图案一样好看而整齐的补丁。两个鼓鼓的大包堆在他身边,只见他一件一件从包中拿出家什来。“原来是补鞋的,这一下可好了。”小王高兴地找出他那双要补的鞋。
大家都送了鞋去补,我向院子里看了好几次,修鞋的人始终埋头拾掇着鞋子,并不在乎寒冷的风像刀子一次次掠过他光着的脚踝。我想等那些堆成一堆的鞋消失后,再拿自己的去补。
天快黑了,“师傅,我的鞋今天还能修吗。”
“太晚了,今天我一定得赶回家。”
“回家,远么?”
“离这儿大概30里路”,他指了指远处已经消融在夜色中一抹淡淡的山影。
“那,我的鞋……。”
补鞋人发紫的面颊上满是疲惫和饥饿。我想起来,从中午到现在他一直坐在院子不停忙碌,同事们请他进屋、喝水吃饭,他都拒绝了。一双干裂的大手,修补着一只只鞋上的裂缝。我听见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这鞋补得好,价格也便宜。
“我明天再来,给你补吧。”
“真的,太好了。”
我并不真的相信,就为了我这一双鞋,他会再走来这儿。我还是坚持送给他两包方便面,让他在路上充饥。
第二天,尽管冻痛的双脚提醒了我修鞋人的失信。但我并不责怪他,生活中的确越来越少有恪守行业道德的服务,失信是最常见的了。何况他的服务让大家都满意了。
可是,我还是又看见了他,修鞋人。第三天我刚起床打开门,他顶着满头的冰珠向我说着没有按时来的原因,还有一些对不起之类的话。那一刻,我感觉到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急忙拿出该补和可补可不补的一大堆鞋子、提包什么的,总不能让人家一大早跑来就补一双鞋吧。他能来,也许也正是为多一些酬劳,我估计我拿出的这些什物,在城里补得二、三十块吧。看来,这个月我得要改改开支计划了。
“都补好了,你看一看。”
补鞋人认真地查看了手边的鞋子和提包,对我说。
“很好。补得真不错!”,我应付着,递过二十五元:“请你收下吧”。
“一共五块钱”他平静地说。
“五块?”
修鞋人开始收拾行装了,看我还站在那儿。“我年年来这儿补鞋,天冷了,没有一双好鞋不方便。”他说,“我家就在城边住,明年我还来,回头见,年青人。”
是这样,他要在城里边补鞋,一天的收入要比在这儿多好几倍呢。五块钱连这来回的路费也不够呀。
我不禁向早来的同事们打听起这个古怪的修鞋匠。同事告诉我,他是个好人,替人补鞋赚的钱都捐助了三个失学儿童。而他孤独一人住在小房子里,日日穿着旧衣服。
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这偏远的矿区,连同他的名字。我想起一首小诗:
人在坎坷的世上行走/怎么能/没有一双好鞋/该钉掌的就钉掌/该补的地方/就补好/我是你们的鞋/我不是路/路却因我而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