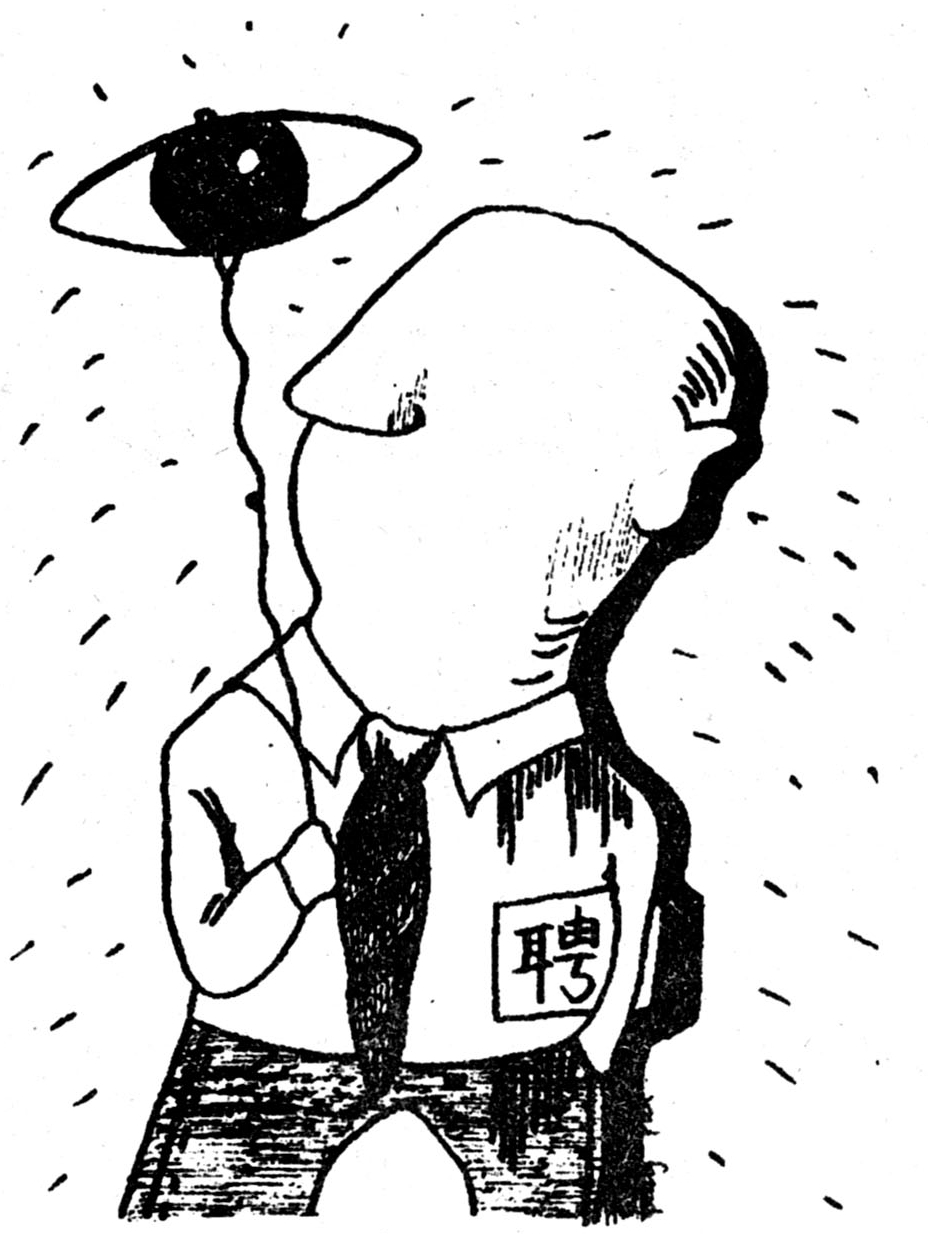[咸阳]石竹
5月9日。当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我扑到父亲的遗体上,哭着啕着说:“大唔。我这以后再也没大(读duo)人看了呀!”那种人生最莫大的失落和伤痛,一并撕裂着我的心。
记得还在解放前,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父亲赶着大轱辘老牛车去换油。那天过一条河,父亲站在车辕上铆足了劲高扬长鞭想一气冲过去。可牛车却搁浅在河中间。父亲急了,一下子跳进水中,肩身扛着车轱辘,手扬长鞭大吼一声,牛车便冲出河漕,上了河坡。等到赶回家,父亲棉裤上的冰块如同铁桶般箍在腿上。父亲的冰裤是在热土炕上暖了大半天才退下来的。自那以后,父亲的小腿上和脚脖上的青筋如同缩身的蚯蚓一般,疙疙瘩瘩地暴出皮肤,每阴天便抽筋似地痛。
还在上世纪60年代,那一年我16岁,那一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弟兄六人和父亲共拉着五辆装得如同小山般的棉杆的架子车往咸阳造纸厂送。吭哧四十多公里,大中午前赶到咸阳城,等排了大半天队交完棉杆返回时,一身的疲劳全集中到了腿上和眼上。实在拉不动了,父亲将五辆架子车连起来,如同一辆小火车一样,父亲一人在前边拉着,我们弟兄则在车上坐着或半躺着。呵!我弟兄就是这样被父亲拉扯大的。
那一年秋天,父亲赶车去北山给生产队拉柿子,却让车压了。父亲腰骨骨折了,在家整整躺了两年。期间去省城的医疗费集体分文未给,误工的补贴更谈不上了。我当时为此愤愤不平,可父亲却说,是我赶车出了事,与集体有啥关系呢!?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以他的宽容和大度对集体的,但集体却没有以良知和仁慈来回报他。
在母亲过世十多年,父亲六十岁时,托叔父给我说,他想办个人。这是我说什么也无法接受的事,可等我过了一段时间回家时,父亲已将一位老人引进了门。我当时真有点懵了。这时,父亲矜持而又为难地说,娃,这是大办的人,你想叫啥就叫,不想叫啥就算了。父亲说到此,咽下一口唾液接着说,你以后愿给我钱就给一点,不给,大也不怪你。父亲这一句话,说得我的泪水实在是难以忍住了。我不知该对父亲说什么好时。那位老人终于上前说,娃,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大的,我那边屋里门前有几棵大桐树,是够给我做棺板,我还有几担小麦,回头都拉过来,足够我俩吃几年,谁能知谁活多少呢!听了此话,我的心颤栗了。情不自禁地上前去,真情地叫了一声姨妈。见此,父亲和姨妈先用惊诧而又满含泪水的眼光看着我,三个人便哭抱一团。
姨妈仅和父亲过了三年,便驾鹤西去了。为姨妈送葬时,父亲并未通知在外工作的我。听人说,在姨妈弥留之际,父亲就用好酒好肉请来村上的相好,求他们一定帮忙埋人。父亲就这样将姨妈送走了。后来我回家,怨父亲不该这样小看了儿子,父亲只说;我说过,不给你们增加负担的。父亲一生似乎是为了干活养儿女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一生的职责,就是用汗水来养育他的儿孙。所以我说,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父亲的血,是靠饮父亲的汗水长大的。
父亲去世后,我的脑海里蓦然就闪现出四个字:“功德无量”
安息吧!父亲,永远活在儿子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