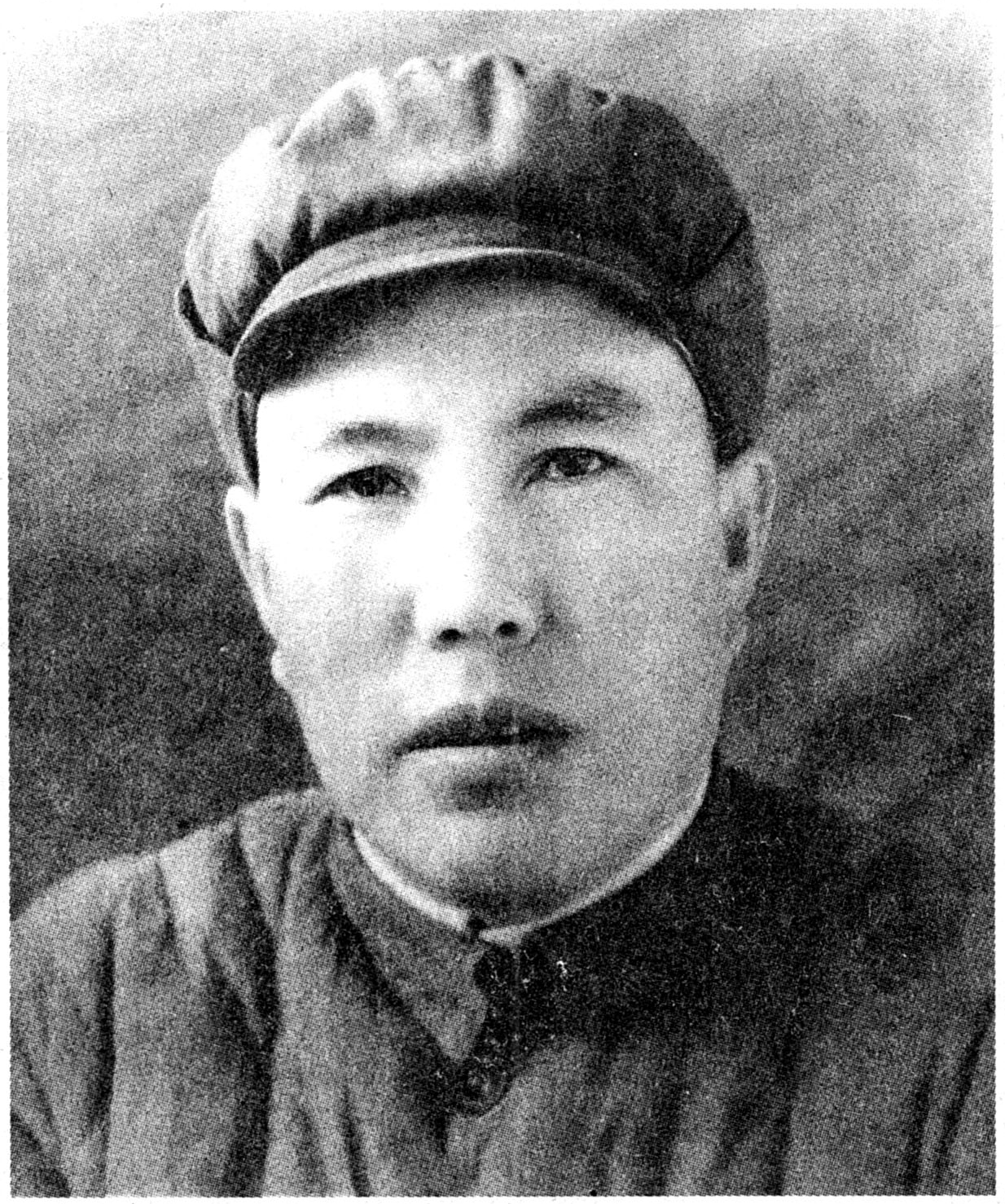二十年前刚迈出校门首次赴京公干,一呆便是几十天,逛过故宫、颐和园的同行陕人们或牵儿挂女或想起“油泼粘面”、“羊肉泡馍”而纷纷发生倦鸟之思。独余凭着一张月票和百十元出差补贴,整日价早出晚归徜徉在京城各处大小书肆野摊之上,大有刘阿斗乐不思蜀之感。直到最后人家带着在西单、王府井采购的“长城风衣”、茯苓饼满载而归时,我的箱包装满书外,还用牛皮纸打了两大捆。迄今书架上的《别林斯基选集》、《果戈里选集》、《激荡的百年史》诸书,都是当年的孑遗。
自从发现北京有诸多的淘书去处,只要一有赴京的机会就奋勇争先。往往是人在车上,心思全在那些书友们传言中的购书场上了。有年作为某刊特约记者被邀去东北开会,归途在京转车仅有半天时间也忙去淘了一堆书。架中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是一次开会期间在宾馆商品部发现,四大册还是当初的5元;《契诃夫小说选》我无下册,就是这次仅用3角钱补齐的。然而由于在一穷单位打工赴京机会少之又少,自费无钱忙于讨生活又无闲,每每为见诸报端的北京五一、金秋等众多书市的消息无法前往徒生遗恨,此滋味当只有好妖娆的靓女错失一件心爱时装、饕餮之徒错失一场盛宴者方可体味。
近年来,由于商品经济侵蚀,京城一家家书肆消失了,一处处地摊随同胡同被赶得无影无踪了,特别是书价暴涨,即使淘得一本好书也每每被背面的天价吓得口瞪目呆,把玩良久往往以怏怏离去而告终。甲申年末,因某机缘得以赴京,在短短几日寒雪猛风中又过了一把淘书瘾。
甫下火车西客站外“拉客”者无数,但见以“前门”相招徕,由于距离琉璃厂近的下意识作祟便下榻于西河沿每位20元的小旅店,然而淘书首战便告失利,海王邨中国书店是我每每必到之处,这次由于拆迁呈半停业状态,已经扫兴大半,而旧书部里昔日定价几毛几元书动辄以百十乃至千元要价,直逼文物已不感惊诧,面积也由当年见到的几百平米后来几十平米萎缩成仅有几架书。几经搜寻还算小有所获,值得一记的是以10元购得《刘禹锡全集》,只是影印太差,字迹斑驳模糊;昔日不值一哂的《太上感应篇》由于索价仅一元也就收入囊中。周围其它几家书店,有的消失了旧书部,有的仅有一两架书只剩下个幌子,拙劣的仿古建筑里,四处是每字“200”、字画数千的治印卖画作坊。睹此不由感喟不但明清以降文人巨子眼中的琉璃厂早杳无踪迹,就是比起前些年也大有今不如昔之叹。
“礼失求诸野”,不料此话应验到了此次淘书之旅。临返回前日陪人去城外北大,从车上发现了知名的“万圣书园”,琳琅满目的图书与沉浸其中的老少读者直觉书香扑鼻而来。前年半价未购失之交臂抱憾至今的《蔡元培全集》,这里仍为全价,考虑到搬动的不易最后仍是放回架上;在一楼降价部购得一本翟晓光编的思想随笔,近五百页售价仅一元,从目录见收有钱理群、朱学勤、秦晖诸先生的几篇大作就叫人感到物超其值。《告别乌托邦》久闻其名,而煌煌三大卷在此店仅以15元获得,殊出人意料之外。
薄暮时分,与游园归来的张君会齐自东门进入北大。方知映入眼帘的所谓“一塌糊涂”的一塔原是水塔,而大名鼎鼎的“未名湖”只是一个小水洼,上面有人在溜冰,不勉感到有些失落。在未名湖畔以塔为背景匆匆留影过,忙在北大找书店。可惜最大的一家因装修而歇业;在邮局旁从一家私人小店以三折购得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再到位于地下的博雅堂书店竟发现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前不久方在《书屋》杂志上看到相关介绍,而今在五四发源地购得此书,结账时又是八折优惠,遂忙让售书的店员小姐盖章纪念,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提着一大包新旧书籍,离开北大校园时天已全黑。凛洌西风中想到此日为农历冬至,虽未随俗吃到饺子,虽未来得及去逛早闻其名的潘家园子,但在严复、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诸先贤思想过的地方淘得一大笔精神食粮,也算不虚此行。 (秦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