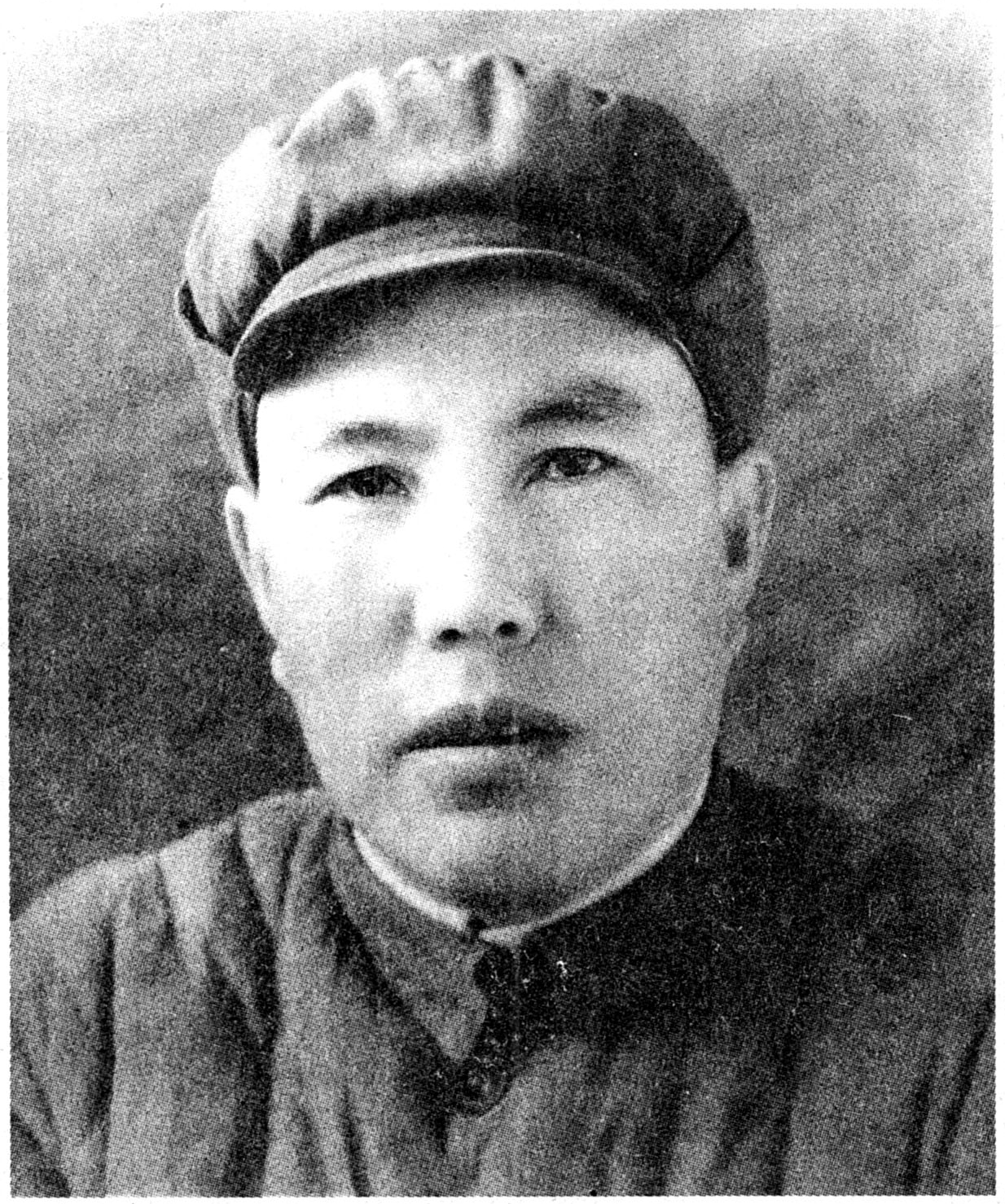编辑“三秦文化丛书”的朋友,日前嘱我编一本小书加盟。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事,立即就答应下来。忙了一阵翻拣复印编排,就成了这一本《长安书声》,应是我第七本书话随笔集了。
与前几本书话随笔来比照,文字“皆与三秦有关,”应该是《长安书声》的特点。既是特点,却也是它的局限。其实,局限也不是坏事,起码可以从这些短文,看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文学和出版方面的一些人和事。虽然零碎,史料方面却还是靠得住的。至于体裁,依然用书话随笔体,想写得平实一些、随意一些。有点实证,也有一点议论:有实证,避免了空冷;发议论,表达自己一些看法。这里边,也少不了有一些辩证色彩的文字,扪心自问,不过是想打捞一点失去的历史记忆或揭开曾被遮蔽的史实的一面,倒不是要与人拗一调和立异鸣高。曾有学者说,现在要鼓励知识分子的质疑精神。质疑当然是应该的,任何时候,实事求是求本求实也是做人的起码品格,做人如此,作文更无论焉。而鼓励这种精神,自属大题目。一种精神要来鼓励,可见有点难度,质疑也还会遇到麻烦的吧。不过,这种鼓励,倒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学术的自由,与以前的一言定谳,万喙息响是难以同日而语了。
说起地域文化,陕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恐怕是一省两制的典型,延安是革命圣地,西安是国统区。从政治层面上,毛泽东同志就用延安西安来代表革命与反动、光明与昏暗、前进与倒退。解放以后,延安文艺研究已成显学,其被关注度与研究成果,可以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研究并美,而延安以外的西安的现代文艺活动就相形见绌得多了,即使在沦陷区文艺研究已然为人注意的今天,它也还是冷而难热。这原因,恐怕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去申说。可以说一说的是,即使在国统区的西安,也还有过一批知名的不知名的志士仁人,在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仪文化传统和根基,只是在近代才日显颓势的地面上耕耘着守护着开拓着,从而维系了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脉在这里未曾中断。可以并不武断地说,这里诚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热土,但也并非被现代文学遗弃的白地。盲目骄傲当然不配,攀附拉扯未免可怜,一味自卑却也不必。作为受惠于这块土地的笔者和有兴趣于此的学人的责任,就是去潜心挖掘去辩证去梳理和认识。
鲁迅先生当年深情殷殷的一段话,时时耳提而命我们:“和我们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三秦文化研究会的同人,正是有志于此,且实施多年的获成果者,在编完《长安书声》的时候,我谨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敬意。
2004年11月24日西安初雪 (高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