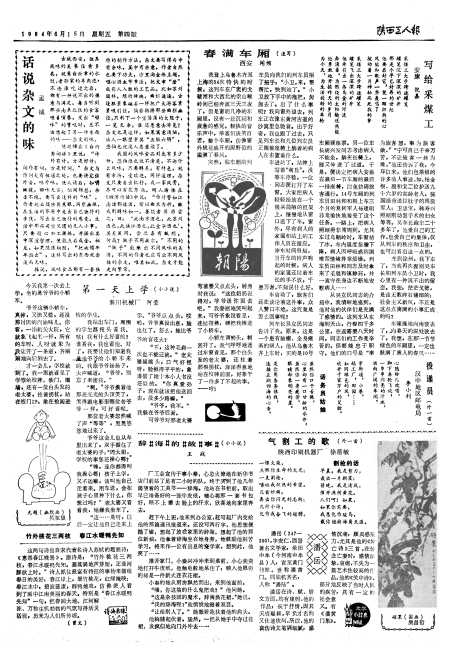
本版导读
话说杂文的味
孟钺
古城西安,独具风味的美餐佳肴多矣,就象白云幸的水饺,老孙家的羊肉泡,不论谁吃过之后,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与满足。每当听到那些南来北往的食客咂着嘴唇,发出“够味”的赞叹时,总不由想起了另一种东西的味——杂文的味。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里说:“诗外有诗,方是好诗;词外有词,方是好词。”杂文与诗词大有相通之处,也要讲究弦外音,味外味,使人读后,如嚼橄榄,回味无穷;似闻锦瑟,余音不绝。要写出这样的“味”,作者就必须独具慧眼,洞察幽微,在生活的莽原中走出自已独特的步伐。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的凡人小事,只要精心加工提炼,开掘出其中深邃哲理,便能点石成金。相反,如果陈陈相因,“把破帽年年拈出”,这样写出的东西就会淡而无味。
据说,风味食品都有一套独特的制作方法,杂文要写得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作者自然也要下功夫,沙里淘金炼主题,呕心沥血布章法,把文章“磨”成引人入胜的工艺品。比如苏州园林,绿竹掩映,曲栏逶迤,古迹胜景象磁石一样把广大游客紧紧吸引住,倘若拆掉那些曲栏幽径,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大院子,一览无余,谁还愿意去游览?杂文也是这样,如果寓意浅陋,让人一眼望穿其“五脏六腑”,恐怕也就没人愿意读了。
我国的风味食品到底有多少种,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不论什么风味,只要醇美,有特色,就有市场,受欢迎。同样道理,杂文只要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尽可以百花齐放。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刚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乎不同故尔。”不同的“做乎”能酿出不同风味的美酒,不同的作者也应写出不同风格的杂文,唯其如此,杂文才能走向繁荣。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