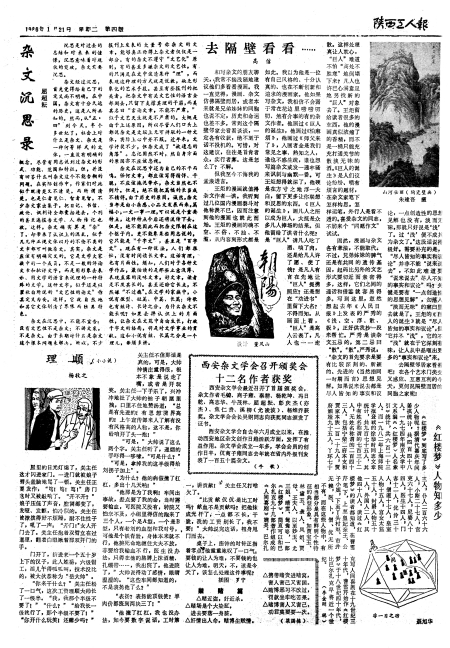
杂文沉思录
屈超耘
沉思是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憧憬,沉思意味着对现状的突破。杂文需要沉思。
杂文经过沉思,首先觉得给自己下的定义尚不明确。在中国,杂文有十分久远的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从“五·四”到今天,半个多世纪了,社会上对什么是杂文、杂文是一种何等样式的文体,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尽管有同志说到过杂文的形式、功能、范围和特征,但,并没有回答什么叫杂文这个不能含糊的问题。在实际创作中,作家们对此似乎既清楚又不清楚。而所谓清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杂文家出集子,把日记、书信、政论、讽刺诗全都囊括进去,个别的甚至连报告文学、人物传记也收。这样,杂文确实算是“杂”了,却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似乎凡几种正规文体以外的不伦不类的文章都可叫做杂文。其实,杂文是应该有明确定义的。它是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不是一般的评论文章和批评文字,而是用形象去表示、用文学的语言来说理的一种特珠的文学。这种文字,似乎还是以翟秋白所说的“文艺性的论文”作其定义为妥。这样,它就自然地和其它文体划清了界限而独具特色。
杂文在沉思中,不能不宣告:没有文艺性不是杂文;不讲文采,不是杂文。由于长期对什么是杂文这个根本问题未解决,所以,不少报刊上发表的大量号称杂文的文章,能够真正称得上杂文者仅仅是一部分。有的杂文不遵守“文艺化”原则,有的甚至多嫌杂文的文艺性,有的只满足在文中谈清某种“理”,而表现这种理的方式就是说教,缺乏形象化的艺术手段。甚至有些报刊的把关者,把杂文中有关文艺性的语言全部删去,只留下支撑其理的干筋,而美其名曰“言论文章,不能不严肃。”似乎文艺天生就是不严肃的。大概是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尽管人们口头上都说杂文是文坛上无可辩驳的一种文体,实际上心中并不服。近年来,文学评奖不少,但杂文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忘记固然不对,然自身方面的原因亦不应该忽视。
杂文在沉思中还为自己的不平而鸣。任何文章,都应该写得精悍、干脆,不应该拖泥带水,杂文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绝不能把篇幅的长当成不精悍。由于历史的原因,诚然,杂文当年是由小杂感、小品文发展而来,篇幅小,一文一事一理,可以说是个重要特点,这种特点今后还将流传下去。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把杂文限制在这个框子内。更不能象某些同志说的,它只能是“千字文”,甚至是“百字文”。现在有一种说法,人们都很忙,没有时间读长文章。这话有理,也有片面性。须知,人们对于各种文学作品,最怕读的是那些立意浅薄、表现直露的没味文章,好文章,读者是不厌其长的。甚至还盼它长点,不然嫌“不过瘾”。在文学的家族中,小说有微型、短篇、中篇、长篇;诗歌也有短诗、长诗之分,为什么杂文不能长呢?如果去掉认识上的片面性,让杂文在文苑中自由生长,打破千字文的格局,将是对文学事业的贯献。这和小说有短、长篇之分是一个理儿,毋须多讲。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