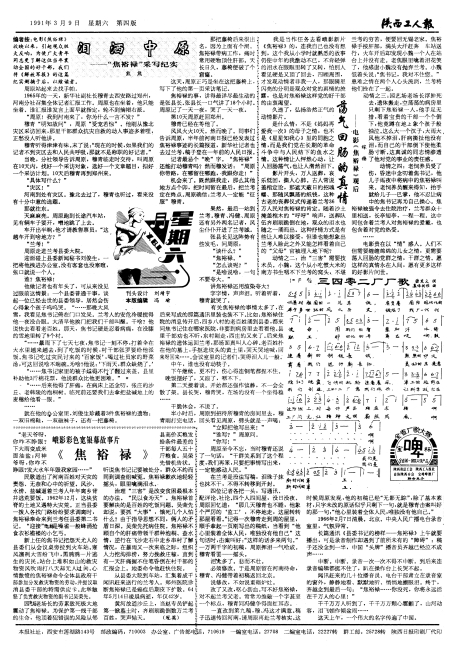泪洒中原
——“焦裕禄”采写纪实
熊熊
编者按:电影《焦裕禄》放映以来,引起观众极大反响,为使广大青年同志更了解这位当年震动全国的好干部,我们将《解放军报》的这篇纪实删摘于后,以飨读者。
周原站起来去找手帕。
1965年的一天,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去西安路过郑州,河南分社召集全体记者汇报工作。周原也在坐着,他只能坐着。谁汇报谁发言上面早就指定,轮不到摘帽右派。
“周原!我到河南来了,你为什么一言不发?”
穆青“明知故问”,周原“受宠若惊”。他刚从豫北灾区采访回来,那里干部群众抗灾自救的动人事迹多着哩,正愁没人听他讲。
穆青听得津津有味。末了说:“现在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记者不到灾区去和人民共呼吸,那就不是称职的好记者。”
当晚,分社领导告诉周原,穆青临走时交待,叫周原在10天内,找好一个采访对象,选好一个文章题目,拟好一个采访计划。10天后穆青再到郑州来。
“具体写什么?”
“灾区!”
河南到处有灾区。豫北去过了,穆青也听过,看来没有十分中意的选题。
那就往东。
天麻麻亮。周原跑到长途汽车站,见有辆车子要开,噌地跳了上去。
车开出半晌,他才请教售票员:“这趟车开到啥地方?”
“兰考!”
周原走进兰考县委大院。
迎面碰上县委新闻秘书刘俊生,一把将他拽进办公室。没有客套也没寒暄,张口就说一个人。
谁?焦裕禄!
他做记者也有年头了,可从来没见过眼前这情景:一个县委普通干事,谈起一位已经去世的县委领导,居然会伤心得象个孩子呜呜哭。……那晚大风雪,我看见焦书记倚在门口发呆。兰考人的安危冷暖搅得他一夜没合眼。大清早他挨门把我们干部叫醒。干啥?他说快去看看老百姓。那天,焦书记硬是忍着病痛,在没膝的雪地里转了9个村。
“……暴雨下了七天七夜,焦书记一刻不停,打着伞在大水里趟来趟去,到了吃饭的时候,村干部张罗要给他派饭。焦书记吃过灾民讨来的‘百家饭’,喝过社员家的野菜汤,可这回说啥不端碗。为啥?他说:‘下雨天,群众缺烧了。’”
“……焦书记家里的被子烂得不行了翻过来盖。县里补助他3斤棉花票,他说群众比他更困难。”
“……后来他得了肝癌,在病床上还念叨,张庄的沙丘、老韩陵的泡桐树。临死前还要我们去拿把盐碱地上的麦穗给他看一眼。”
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刘俊生珍藏着3件焦裕禄的遗物:一双旧棉鞋,一双破袜子,还有一把藤椅。
那把藤椅后来很出名,因为上面有个洞。焦裕禄带病工作,痛时常用硬物顶住肝部。天长日久,藤椅便破了个窟窿。
这天,周原正巧是坐在这把藤椅上,写下了他的第一页采访笔记。
焦裕禄的事,讲得最详尽最生动的是张县长。张县长一口气讲了18个小时。周原记了一天一夜,哭了一天一夜。
第10天周原赶回郑州。
穆青已经在等他了。
风风火火10天。然而晚了。同事们告诉周原,半年前河南日报已经发表过焦裕禄事迹的长篇报道,新华社记者也去过兰考,稿子登在一年前的人民日报。
记者最忌个“晚”字。“焦裕禄”还能打动穆青吗?然而穆发话:“周原你带路,在哪留往哪跑,我跟你走!”
机会来了。既然跟我走,那么其他地方点个卯,把时间留在最后,把兰考定在终点。周原确信:兰考人一定能“征服”穆青。
果然,最后一站到兰考。穆青、冯健、周原还有另外两名记者,风尘仆仆开进了兰考城。
张县长见这阵势有些发毛,问周原:
“谈什么?”
“焦裕禄。”
“怎么谈呢?”
“是啥说啥,一句不要夸大。”
讲焦裕禄还用渲染夸大?
字字情,声声泪。听着听着,穆青就哭了。
有关焦裕禄的事情太多了,在后来写成的那篇通讯里装也装不下。比如:焦裕禄住院的消息传开后,四乡八村的老百姓涌到县委,都来问焦书记住在哪家医院,非要到病房里去看看他。县里干部劝也不听,东村刚走,西庄的又来了。后来焦裕禄的遗体运回兰考,那场面真叫人心碎。老百姓扑在他的墓上,手抠进坟头的黄土里,哭天哭地喊:回来呀回来……。会议室里的记者们,哭得泪人儿一般。
中午,谁也没有动筷子。
下午继续。更不行,伤心得连钢笔都捏不住。
晚饭摆好了,又凉了,咽不下。
第二天接着谈。开始都还强作镇静,不一会全散了架。县长哭,穆青哭,在场的没有一个坐得稳
干脆休会,不说了。
半小时后,周原到招待所穆青的房间里去,穆青刚打完电话,回头看见周原,劈头就是一声喝:“立即把他写出来!”“谁写?”周原问。“你写!”
周原至今不忘,当时穆青还说了一句话:“干群关系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再笨,只要把事情写出来,一定能感动人民。”
在兰考是没法写稿,泪珠子抹也抹不干,不得不转移到开封。
四位记者各把一头,写通讯、配评论、社论。四个人四间屋,没日没夜。周原回忆道:“那几天穆青也不睡,他象个严厉的‘监工’,不停地走,这屋转转那屋看看。”记得一次穆青走到周的屋里,顺手拿起一页刚写出的稿纸,当看到“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时,击案叫好:“这样的话多来两句。”一万两千字的初稿,周原挥泪一气哈成。穆青看罢——摇头。
泪太多了。悲而不壮。
必须修改。于是周原留在河南待命,穆青、冯健带着初稿返回北京。
说修改,不如说重砌炉灶。
改了又改,呕心沥血。写不好焦裕禄,对不起兰考父老。常常为推敲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穆青同冯健争得面红耳赤。
一直改到第九稿,穆、冯这才满意。稿子迅速传回河南,请周原再赴兰考核实。这时候周原发现,他的初稿已经“无影无踪”,除了基本素材,只字未改的原话似乎只剩下一句,就是穆青击案叫好的那一句:“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1966年2月7日清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里,气氛异常。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上午就要播出,可是录音制作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稿子还没念到一半,中国“头牌”播音员齐越已经泣不成声……
中断。中断。录音一次一次不得不中断。到后来连录音编辑都挺不住了,趴在操作台上长哭不起。
闻讯赶来的几十位播音员、电台干部肃立在录音室的窗外,静静地看、默默地听、悄悄地擦眼泪。终于,齐越念到最后一句:“焦裕禄……你没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千千万万人听到了,千千万万颗心震颤了,山河动容,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天上午,一个伟大的名字传遍了中国。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