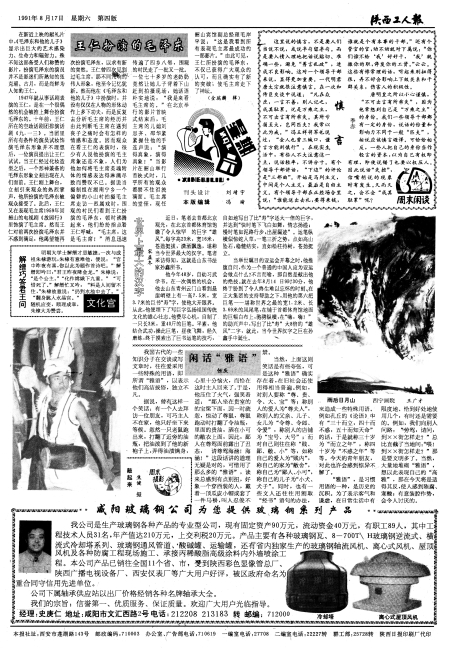闲话“雅语”
恒庆
我国古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交谈或写文章时,往往爱采用一些特殊的用语,即所谓“雅语”,以表示他们高洁拔俗,独立不凡。
据说,曾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去拜访一位朋友,可巧主人不在家,他只好坐下来等候。忽然一只老鼠跑出来,打翻了近旁的油瓶,把油泼到了他的新袍子上,弄得油渍满身,心里十分恼火,而恰在这时主人回来了。于是,他压住了火气,强笑着道:“鄙人坐在贵室的的宝梁下面,因一时疏忽,惊动了尊鼠,尊鼠跑动时打翻了令油瓶,里面的贵油,洒在小可的敝衣上面,因此,鄙人在尊驾面前露出了丑态,请尊驾海涵!海涵!”这段话讲的道理无疑是对的,可惜用了那么多的“雅语”,读来总感到有点别扭,好象一个穿西装的人,戴着一顶瓜皮小帽或套了一件马褂,叫人忍俊不禁。
当然,上面这则笑话是有些夸张,可是这种“雅语”确实存在着,在旧社会还使用得相当普遍。例如,对别人要称“尊、贵、令、大、宝”等;称别人的爱人为“尊夫人”,称别人的父亲、儿子、女儿为“令尊、令郎、令爱”,称别人的店铺为“宝号、大号”;而对自己则往往称“贱、鄙、敝、小”等,如称自己的爱人为“贱内”,称自己的家为“敝舍”,称自己为“鄙人、小可”,称自己的儿子为“小犬、犬子”。同时,也有一些文人还往往用割取“经书”语句的办法,来造成一些特殊用语。例如孔丘的《论语》中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话,于是就称三十岁为“而立之年”,称四十岁为“不惑之年”等等。今天的青年朋友,对此也许会感到惊异不解了。
“雅语”,是习惯用语的一种,是历史的沉积。为了表示客气和谦虚,在日常生活中有限度地、恰到好处地使用几个,有时还是需要的。例如,我们向别人问路:“劳驾,请问,到××街怎样走?”总比直截了当地问:“喂!到××街怎样走?”那是要文明多了。当然,大量地堆砌“雅语”,想以此表现自己的“高雅”,那在今天将是适得其反,使人感到陈腐、寒酸;有意装腔作势,会令人讨厌的。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