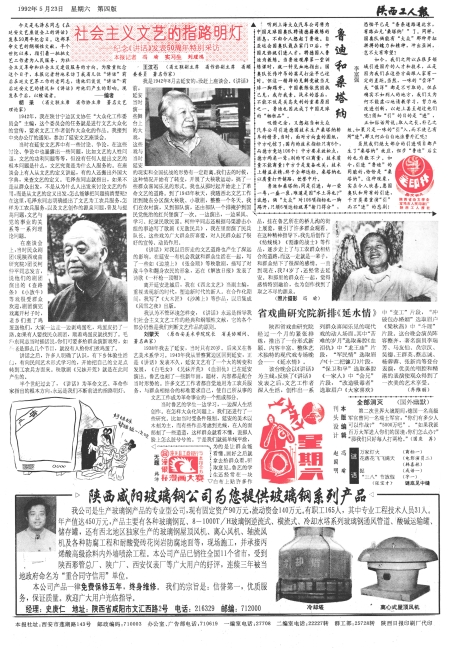社会主义文艺的指路明灯
——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特别采访
本报记者 冯瑜 实习生 刘瑾鸿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纪念日。这部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半个世纪以来,指引着一批批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为隆重纪念这个日子,本报记者特地采访了我省几位“讲话”前后在延文艺界工作的老同志,请他们谈谈“讲话”前后延安文艺的情况和《讲话》对他们产生的影响。现发表于后,以飨读者。——编者
胡采 (省文联主席 省作协主席 著名文艺理论家)
1942年,我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任“大众化工作委员会”主编,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宣传,要求文艺工作者创作大众化的作品。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当时在延安文艺界中有一些讨论、争论,在这些讨论、争论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文艺的人性问题,文艺的功利问题等等,但没有任何人提出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文艺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在座谈会上有人从文艺的定义讲起,有的人还搬出外国大字典,来查文艺的定义。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如果不是从群众出发,不是从为什么人出发来讨论文艺的作用,而是从文艺的定义出发,怎么能够把问题搞清楚呢?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怎样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文艺与党的事业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在座谈会上,当时民众剧团(现陕西戏曲研究院)团长柯仲平同志发言,说他们的剧团演出的《查路条》《小放牛》等戏很受群众欢迎,剧团演完戏离开村子时,老乡们煮了鸡蛋送他们,大家一边走一边剥鸡蛋吃,鸡蛋皮扔了一路。如果有人要找民众剧团,顺着鸡蛋皮就找到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插话说,你们可要多给群众演新戏呀,如果老是那么几个节目,就没有人给你们煮鸡蛋了。
讲话之后,许多人明确了认识,有下乡体验生活的,有向民间艺术形式学习的,开始把自己的立足点转到工农兵方面来。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在此间产生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讲话》为革命文艺、革命作家指出的根本方向,永远是我们不断前进的指路明灯。
王汶石 (省文联副主席 省作协副主席 省顾委委员 著名作家)
我是1942年8月去延安的,没赶上座谈会。《讲话》前,延安当时演一些舞台上的大戏,这些戏与当时延安的现实和全国抗战的形势有一定距离。我们去的时候,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转变,开展了大秧歌运动,搞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我也从那时起开始走上了革命文艺的道路。到了1943年秋天,我随西北文艺工作团到陇东分区演大秧歌、小歌剧,整整一个冬天。我们在农村演,又到部队演,还由部队一个排掩护到国民党统治的红兴堡演了一次。一边演出,一边采风、学习、纪录民歌民谣。柯仲平同志还根据马渠游击小组的事迹写了歌剧《无敌民兵》,我在里面演了民兵队长。这些戏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对人民群众起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
《讲话》对我以后所走的文艺道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延安一有机会我就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写了一些如《边境上》《张金顺》等秧歌剧,描写了对敌斗争和翻身农民的形象,还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诗歌《一杆枪一顶帽》。
离开延安进城后,我在《西北文艺》当副主编,重视表现新的时代,塑造新时代的新人。在合作化期间,我写了《大木匠》《沙滩上》等作品,以后集成《风雪之夜》出版。
我认为不管环境怎样变,《讲话》永远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经典和纲领性文献,它的各个部分仍然是我们判断文艺作品的原则。
刘蒙天 (原西安美术学院院长 省美协顾问、著名画家)
1938年我去了延安,当时只有20岁。后来又在鲁艺美术系学习。1943年我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正是《讲话》发表不久,延安文艺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和发展,《白毛女》《兄妹开荒》《血泪仇》已在延安演出。鲁艺也刻了一些新年画,题材、内容都是配合当时形势的。许多文艺工作者都自觉地用为工农兵服务,与群众相结合的标准要求自己,使自己所从事的文艺工作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时鲁艺的学生一边学习,一边深入生活创作。在怎样大众化问题上,我们还进行了一些研究。比如当时受条件限制,延安的美术以木刻为主,而有些作品考虑到光线,在人的面部刻了一些道道,这样群众就看不懂,说那人脸上怎么脏兮兮的。于是我们就搞单线平涂,为的是让群众能看懂。画好之后就拿去给群众看,听取意见。鲁艺的学生还经常在一块7白布上贴许多作品,挂在鲁艺所在的桥儿沟的街上展览,吸引了许多群众观看。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我先后创作了《纺线线》《割漆的战士》等作品,逐步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而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和群众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一直到现在,我74岁了,还经常去延安。和那里的群众在一起,觉得感情特别融洽,也为创作找到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照片摄影冯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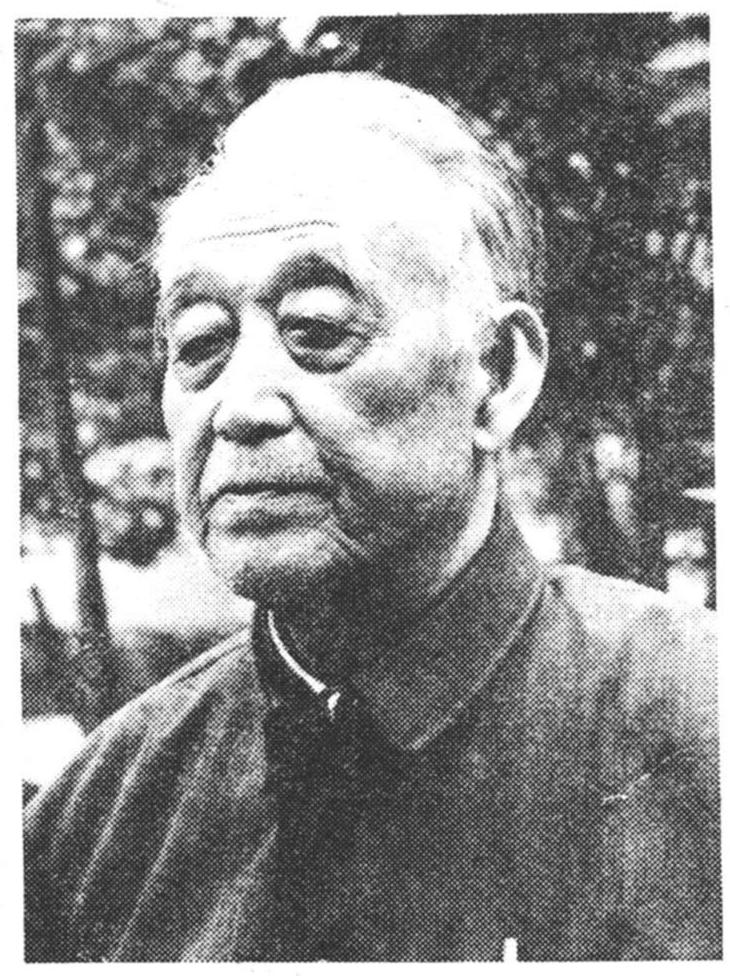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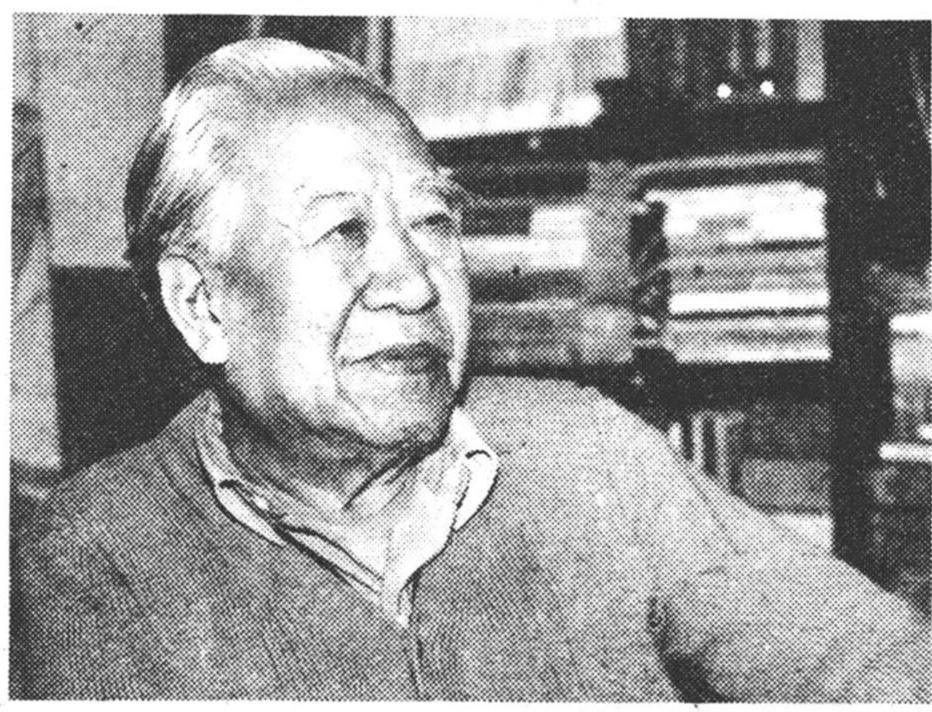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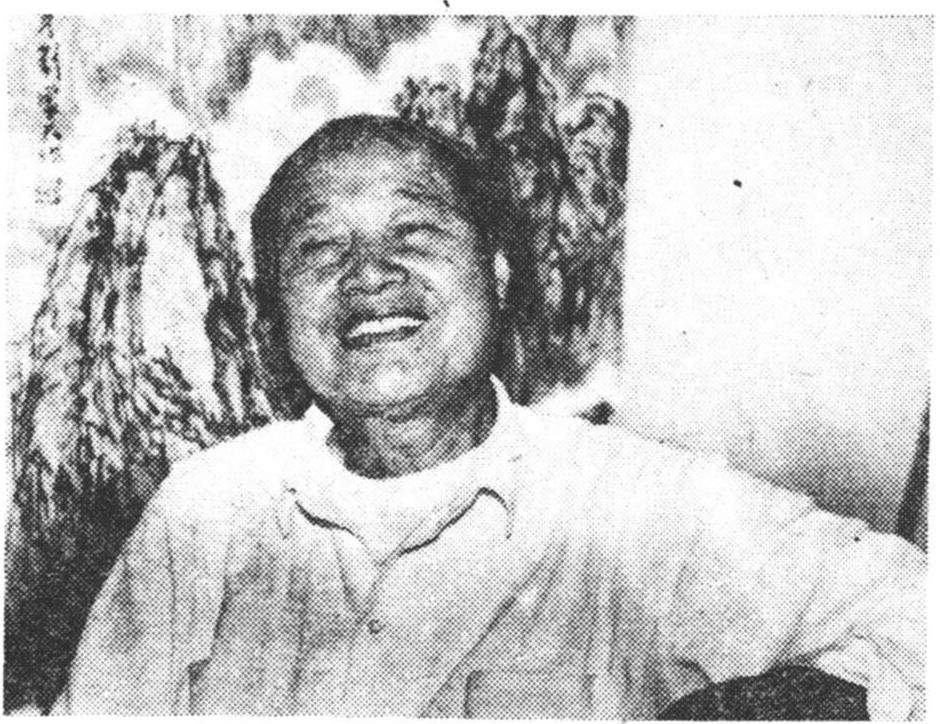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