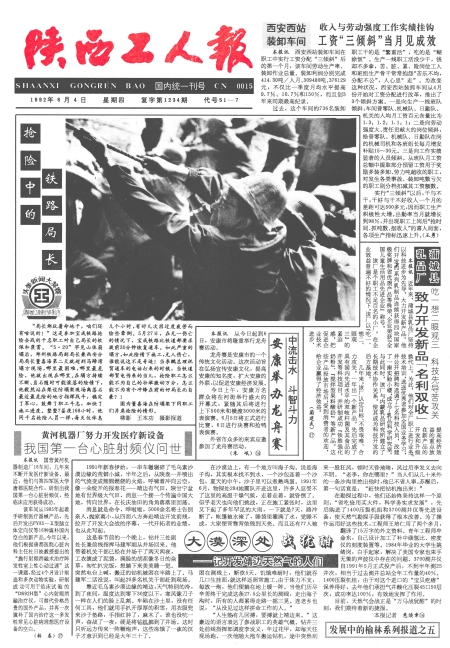
发展中的榆林系列报道之五
大漠深处战犹酣
——记开发靖边天然气的人们
1991年新春伊始,一串车辙辗碎了毛乌素沙漠边缘的荒僻小城,半年之后,从陕叁一井喷出的气流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焰,呼啸着冲向云空,像一朵绽开的报春花——靖边有气田,陕甘宁盆地有世界级大气田,消息一个接一个传遍中国大地,传向世界,在长庆油田的角角落落里回荡。
消息就是命令,哗啦啦,5000余名将士告别亲人,抛家离小,从四面八方奔赴靖边开发前线,拉开了开发大会战的序幕,一代开拓者的业绩,也从此写起。
这是春节前的一个晚上,钻井三处副处长兼前线指挥马建军刚从井场回来。他带着机关干部已经在井场干了两天两夜,工衣滚成了泥袋,满脸的胡茬像冬日的杂草,匆忙扒完饭,想躺下来美美睡一觉。突然电台上喊,搬迁的钻机被困在半路上了。马建军二话没说,叫起20多名机关干部赶到现场。
靠近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靖边,天气特别的冷,到了夜间,温度达到零下30度以下,寒风像刀子一样在人们的脸上乱割。车陷在沙土里,没有任何工具,他们就用手扒开厚厚的积雪,用衣服兜来沙子垫路,手指红肿了,麻木了,谁也没吭一声,奋战了一夜,硬是将钻机挪到了井场。这时只听远方传来一阵鞭炮声,这些冻饿了一夜的汉子才意识到已经是大年三十了。
在沙漠边上,有一个地方叫海子沟。说是海子沟,其实根本找不到水,一个沙包连着一个沙包,夏天的中午,沙子里可以煮熟鸡蛋。1991年6月,物探处284地震队开进这里,许多人忍受不了这里的高温干燥气候,走着走着,就昏倒了。似乎老天也向他们挑战,正在施工紧张时,这里又下起了多年罕见的大雨,一下就是7天,路冲断了,帐篷被水淹了,睡袋里灌满了水,觉睡不成,大家便背靠背依偎到天亮。而且还有77人被困在测线上,断炊5天。饥饿难耐时,他们就吞几口生挂面,就这样还照常施工。由于体力不支,每放一炮,他们便躺在地上缓一阵。当他们历尽辛苦终于完成这条27.5公里长的测线,走出海子沟时,所有的人都累得走路一摇三晃。连老乡也说:“从没见过这样拼命工作的人。”
“人生能有几回搏,要搏就上靖边来。”这豪迈的语言表达了参战职工的英雄气概。钻井三处前线指挥部调度李发义,年过花甲,却每天往现场跑。一次他随大拖车搬运钻机,途中突然刮来一股狂风,顿时天昏地暗,风过后李发义去向不明。“老李,你在哪里?”当人们从几十米外的一条沙沟里挖出他时,他已不省人事。苏醒后,第一句话竟是:“赶快把钻机拖出来!”
在勘探过程中,他们还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省吃俭用买大件,科学务实求发展”,先后购进了1400压裂机组和3700测井仪等先进设备,使天然气勘探手段获得了根本改善。为了操作运用好这些技术,工程师王培仁用了两个多月,翻译了15万字的外文资料。青年工程师牟金东,自己设计加工了补中碳氢比、密度仪的刻度装置等。1984年毕业的大学生姚绪岗,白手起家,解决了美国专家也束手无策的声波仪中存在的问题。3700测井仪自1991年5月正式投产后,不到半年测25井次,相当于过去测井总站全年工作量的40%。1400压裂机组,由于对这个进口的“宝贝疙瘩”保养得好,去年他们承担气井酸化压裂45口50层次,成功率达100%,有效地发挥了作用。
目前,天然气会战正是“万马战犹酣”的时刻,我们期待着新的捷报。
本报记者 惠焕章?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