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问题
文/魏雅华
导言
稿酬问题眼下变得如此尖锐,变得非得展开一场大讨论不可,因为它已经变得与我们目前这个商品社会和商品时代如此不协调,严重地影响到一个如此重要的社会阶层的生存问题。
在这件事上,人们并未象在别的事情上一样,等红头文件。而是悄悄地,却相当积极地动作着。1990年由国家版权局所颁布的“书籍稿酬暂行办法”还在“暂行”着,便已不那么管用了。至少已有一大半被摈弃了。它的修订亟待进行。
积重难返的后遗症
我国的稿酬制度建国四十多年来,曾多次修订,大起大伏。50年代初,我国仿效苏联,原则上根据“著作物”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计酬,并参考苏联按版次计酬的办法,但付酬的标准仅为苏联的五分之一。尽管那时我国实行的就是低工资、低稿酬、低消费的制度,但这个标准仍能使著作人获得较可观的收入。(当然,那时中国一年只出几部,甚至几年才出几部长篇小说,这便使每部长篇小说问世都有相当大的印数)。
从1958年到1965年,“反右”斗争后,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对“知识产权”和“著作权”几乎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于是,国家制定了统一的稿酬制度,一律按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计酬。后来,又将本来就很低的付酬标准一降再降,又索性取消了印数稿酬。
1966年后,这种极左思潮达到了顶点,完全取消了稿酬,甚至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连文章的署名也一并取消。或是署以××写作组集体创作,出现了确属“空前绝后”可笑可悲荒唐荒诞的大闹剧。
1977年后,国家尽管恢复了稿酬制度,但只是象征性的付一点酬。1980年5月,中宣部以(1980)14号文件,转发了国家出版局制订的《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将1977年的“补贴”标准,从每千字2至7元提高到3至10元。1984年提高到6至20元。1990年,国家版权局颁布了“文革”后的第4个“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著作稿酬从每千字6至20元提高到每千字10到30元。而这个标准也才刚刚恢复到50年代初的水平,可时光却不会倒流,90年代的物价已是50年代初的10倍!也就是说,现在提高了4次的稿酬,也只是50年代初的十分之一!
这种低稿酬导致了中国稿酬与国际稿酬的巨大反差。世界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是不养作家的。可话又说回来,如果稿酬制度合乎市场规律,符合其商品价值,又何须谁来养?
中国的作家为什么穷?是他们不勤奋,还是他们智商低?
国外的出版商在千方百计地,或他们亲自上门,或委托代理人上门索搞,由于中国搞酬极低,他们的开价便乘虚而入,一等作品,三等价格,就这也3至5万美金不等。而这个数字,对嗷嗷待哺的大陆作家,已是一夜暴富的天文数字了。
这种畸形的低稿酬制度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谁都知道,一部书的质量,基本上是由文稿的质量决定的。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书的成本(硬件)出厂价只是书价的百分之二十七,而作者的劳动只得到书的价值的百分之三——百分之四,出版社所得为百分之五左右,其余利润均被书商或书店所得!流通环节竟拿走了书籍收费的百分
之六十!
这就是富书商与穷作家的奥秘。
写书的不如卖书的。
作家的地位不如书商的地位。
作家的贫穷已经到了啼饥号寒,需要乞求施舍的程度。
国家一级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英年早逝,他患病期间,医药费无处可报,由省委宣传部特批专款报销,死后清点其财产,存款刚够还债,其资产为零。
路遥一生勤奋多产,生活节俭刻苦,然清贫如此!
而陕西的另一位国家一级作家邹志安,死后《文学报》发起为其募捐,以救济其遗属。作家的贫寒,令人痛心疾首!
这些文坛骄子,尚且如此,其它文化人的穷苦,可想而知。难怪文化人有穷途末路之感。弃文从商者众,另谋生活去也!
该不该与国际“接轨”?
我国现行的稿费制度至今尚沿袭着“按劳分配”的基本指导思想,即按照支付的劳动付给报酬,付出的劳动多,则报酬多,反之,则少。在这个慨念中,缺少了劳动的价值。尤其是对复杂劳动。
美国的稿酬标准从每个字0.5美分到7500美金,跨度150万倍,而我们的稿酬跨度只有2倍。劳动的质量何以体现?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上的巨大差异何以体现?
国际上最通行的稿酬标准是版税制,即按图书发行总价值的适当百分比付酬,最通行的为百分之十左右。如果中国也照此执行,何愁作家不富?
试举一例,笔者一篇文章有幸为一家《文摘》所转载,该刊发行每期320万份,每本定价1元,若按国际标准付酬,每期应支付32万元稿酬,则每千字稿酬应为4200元,笔者6千字的文章应得稿酬为2.52万元。而此后,此刊又出版了3种不同版本,故此文应得稿酬为7.56万元。何愁作者不富?而实际上笔者仅得搞酬120元。
此文还曾被另一家《文摘》刊物所转载,此家刊物发行量也不小,估计在20万份以上,却仅付酬30元。该刊来信说,他们的标准是每千字5元。而且也是依据红头文件的。
还有一家文摘刊物,转载了笔者一部6万字的作品,仅付酬180元,还说他们支付的是高稿酬。也是依据红头文件的。笔者一怒之下,郑重宣布与该刊断交,严禁该刊再转载笔者的作品。(每千字仅付酬3元。)
而现行的稿酬标准中的有些条款则更加让人弄不懂了,比如“对由汉文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对原著作者不付稿酬”,再如,“编选不同著译者的报刊文章合集出版,只付基本稿酬,不付印数搞酬”。“出版社约请多人撰写,单篇独立的合集,只付基本稿酬,不付印数稿酬。”这些规定,连其指导思想都让人莫明其妙。
印数稿酬过低甚至没有,导致书商肥而作家瘦,是对作家、著作权人的一种掠夺。实际上,印数是体现劳动价值最重要的参数,在每一本书中,都包含着著作权人的劳动,付酬当然是必须的。
前不久,报载南韩一位女作家因2部畅销书而成为亿万富婆,稿酬为总洋的10%,总发行量为100万册。若如此取酬,中国作家中至少有100个亿万富翁。
琼瑶一年也不过推出一两部长篇,三四十万字,何以年收入超过300万元港币?其大部分收入为重版稿酬。
若能如此,作家何须“下海”?何须“曾经沧海难为水”?作家莫非不创造财富?作家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
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印了160万册,每本书定价为5.90元,总洋高达896万元,据悉,稿酬为百分之六,她应得稿酬为53.76万元。
有人说,她成功不在曼哈顿,这是真的。
然而,版税制的付酬办法,尽管已被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所接受,但至今并无立法依据。
面对商品大潮,不改也得改了。
进入1994年,旧的稿酬制度,不改也得改了。
当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在完成了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化,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时候,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消费层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报纸、杂志更加商品化。其竞争更加激烈,首先是各报竞相出版“周末版”、“月末版”以期增加印数、扩大市场,争夺读者。其次是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的各种期刊和小报,也加入了这个竞争的行列。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好稿、信息量大、题材重大、可读性强的稿件就必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俏货。加之各出版社亦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能带来巨大济效益的畅销书稿被到处狩猎、精明老练的书商们竭泽而渔,于是,便竞相加码提价,加入了争夺者的行列。
然而,生产一篇好稿,谈何容易?好稿自有好稿的投资。一篇好稿,题材热门,信息量大的热点新闻,并非作者坐在家里,拍拍脑门,一杯浓茶,几枝香烟写得出来的。常常要作者踏破铁鞋,敲开一扇扇不开启的门,寻找一个个不回家的人,受尽从门里被赶出去,又从窗户里钻进去的热脸冷屁股的磨难,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这样的稿,又一再浓缩,才成精品的,自然身价也高,岂是每千字二三十元打发得了的?
实际上,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均已打破了1990年国家出版局的“暂行”标准。在报纸类中,广州的《南方周末》已首先打出每千字100元的稿酬标准。杂志类中,陕西的《女友》也已将稿酬提高到每千字100元。而这两家报刊、杂志也确实从中尝到了甜头,均已双双登上报刊、杂志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发行量突破或直逼百万大关。
其实,主编们心里明白,就是将稿酬提高到每千字200元,又有几个大洋?与报纸、杂志每期的总成本和总收益相比,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微不足道。然而对报纸期刊的质量的影响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小看不得。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
在对畅销书稿的争夺中,书商更为灵活而精明,因为他们的商品意识更强。并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更加洞若观火,从而会更快更有效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对策。在书商与出版社的争斗中,优势和劣势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书商有更精明的办法收罗好稿,他们可以预付稿酬,他们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出书速度。但是,出版社有可靠的信誉和更雄厚的实力,这种竞争对繁荣出版事业有利,对著作权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利。
1993年9月,深圳举办的中国首届优秀文稿拍卖会,更是将书籍稿酬推向市场的重大步骤,是中国文化市场的一个大喜讯。
当内地的作家们还自命清高地在报刊上争论文稿是不是商品的时候,具有超前意识的深圳的拍卖会的重槌已在台面上敲响,并且极明快、极简洁,极响亮地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尚需一提的是著作权人的个人所得税,尽管对此文化界反映强烈,文化界的人大代表一再提出意见,《文学报》也曾以头版地位报道降低税率的消息,但税收部门的通知上仍毫不客气地按百分之二十征收!这个税率比个体工商户的税率还高出百分之三百!又是何道理?
个体户们早已视作家为“文丐”了,可税务局却视作家为“大款儿”。要不,何以得如此?若是税务局视作家为“文丐”,而个体户们视作家为“大款儿”,岂不善哉?
阿弥陀佛!
更新观念刻不容缓
在稿酬问题上:有许多现象更加引人深思。
比如书刊的封面设计,按照出版社的规定,一个封面的稿酬只不过几十元而已。可“货卖一张皮”,这件事早已率先被书商们所认识,读者见到一本书或一本刊物,第一眼看见的是封面。尤其是在眼下的书报摊上,群芳斗艳,百花争辉,封面若不赢人,便难以得到读者第二眼了。
于是,书商们便打出了“一眼千金”的牌,设计一个封面,稿酬1000元。而有些刊物甚至悬尝采用封面一个,2000元稿酬。
这张牌一打出来,出现了几个效应。一是高手们趋之若鹜,二是出版社的美工们躺倒不干。于是,被商品规律所驱赶的总编们也只好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悬尝千金,寻求封面。这便是市场规律!它准确无误地显示劳动的价值。它不承认支付的劳动,只承认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出力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出力。
这原是体力劳动对脑力劳动的愤懑不平。但这是事实,是劳动价值对劳动报酬的一种效应。须知在市场规律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支付的劳动数量,而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劳动质量。
复杂劳动怎么能与简单劳动等值?
是否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创造1000元财富,与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创造10元财富的人领取同样的报酬才算公平?
比如音乐家们,在知识产权上,他们更惨,一个产品走俏,可以100万、1000万装入实业家的口袋,一本书走红,著作权人亦可几千、几万元入帐,可作曲家们呢?“十五的月亮十六元”便是最生动的写照。
如果说,人们口头传唱是无法向词曲作家付酬的,那么许多明明是商品的生产厂家却也藐视词曲作家的权益。近几年来,许多音像出版社发了大财,聚敛了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和资产,他们给歌星们一只歌可以高达数千元的报酬,而词曲作家却只付几十元,十几元,而且也是振振有词,有凭有据地说,这是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他们取的还是上限,支付的是高稿酬!
而广播电台、电视台根本就不付酬,虽然他们每年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地收入广告费,却说他们是“非赢利单位”,播出电视、广播节目是不向听众观众收费的。
关于这个问题,国外是早已解决了的。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国际版权公约对此类问题早已有明文规定,只是中国人历来的惯性很大,于是,掉头和刹车便都很难。难也罢,只要努力便行。而且这个头总要由南方来带。最近,广东电视台便为几位著名的词曲作者一次付了一笔很可观的稿酬,算是个开头儿吧。即便如此,到底给了词曲作家们一个美好的梦。
希望这个进程快些,再快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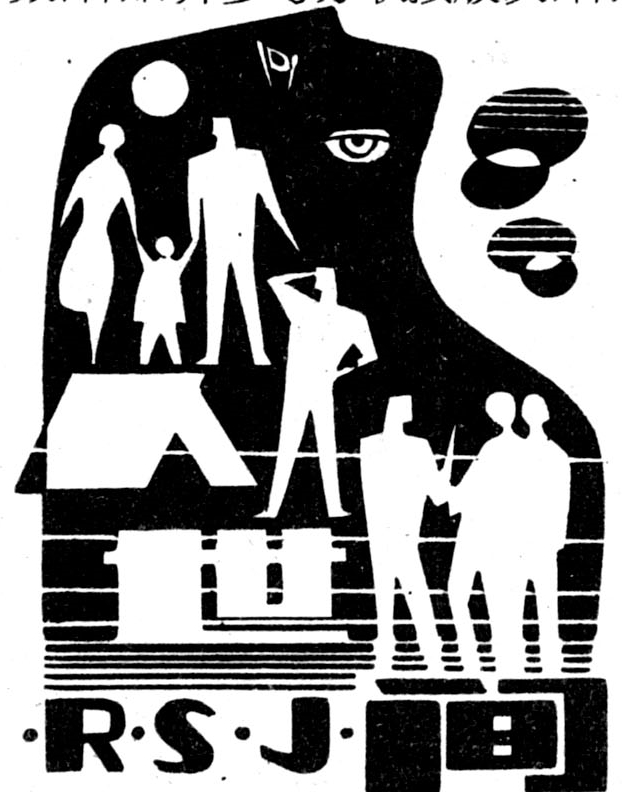
刊头设计/董凤山
本版编辑/周矢

本版速写 陶炳林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