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平坎坷大道
——记职丁艺术家王宪民
文/毛杉
1968年,王宪民的父亲被扣上资本家的帽子关进了牛棚,母亲扯着四个未成年的儿子流放到渭北高原合阳的一个小山沟里当农民。
王宪民是老二,那年,他不满15岁。哥哥是个残疾人,大弟12岁,小弟弟只有9岁。
贫穷的小山村,一个精壮的全劳力每天只挣2角柒分钱,王宪民只好扯着大弟弟,跟着当地农民到山里去打柴,翻坡爬沟,往返一百多里,凌晨二点出发,晚上月上东山才能回来,两个孩子心沉,砍了一百多斤柴,却担不回来,一路撒弃,回来时每人肩上仅剩下20来斤。母亲看到儿子被柴担磨破的双肩,哭成泪人儿。王宪 民却说:“娘,别哭。我们多跑几趟就练出来了。”果然,一个月后,小兄弟俩竟然将三百多斤柴禾从山里用架子车拖回来了。除了自家用,还能到集镇上换回点钱来。
可是,在大上海生活多年的母亲承受不了贫困的折磨竟身染重病。宪民用一辆架子车拉着母亲在沟塬里走了50多里,将母亲拉到县城,让弟弟陪母亲回西安治病。这一走就是八个月。王宪民又要照顾残疾的哥哥,又要经管年幼的弟弟,还要没黑没明地在地里干活,挣工分。15岁的孩子充当了大人也难以承担的角色。然而,如此艰难的生活,竟没有能使他热爱艺术的心火熄灭。他编快板,演样板戏,在村里还挺有名气。两年后,音乐学院毕业,在县剧团当琴师的姐姐结婚了。靠着姐夫的帮助。他们全家迁到了宝鸡,王宪民也续上了中断的学业,在虢镇中学上学。生活有了一点转机,王宪民搞文艺的热情更高了。他吹小号,跟姐姐学拉二胡,很快成了学校的文艺骨干,由他牵头,学校拉起一支管乐队,把个山城宝鸡县吹得风风光光,大小会议都会让他们去助威。两年以后,王宪民又以知青身份再次下乡当了农民。插队的是个位于铁路沿线的比较富裕的农村。王宪民的艺术才能得到重视与发挥,编戏、演戏、吹号、拉琴、王宪民在方圆数十里都是名角儿,并且在县上、地区和省上演出中多次拿奖。到了1977年,各单位招工,王宪民竟成了几家招工单位争夺的对象,最终,王宪民选择了铁路大修工程队,在秦岭山中修路基,换枕木。半年后,调到队部当了工会干事。王宪民天资聪颖,对艺术的悟性很高,学什么像什么,文艺演出行中十八般武艺都能来两下。1978年,他代表宝鸡地区参加省上汇演,演出西府曲子《赎女婿》。汇演期间,他看了石国庆演出的独角戏《秦腔歌舞与离婚》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他跑到石老师的学校去拜师求教,又将石老师的节目录下来,反复练习。以后,石老师演一个,他学一个,不久,他就被人称为“铁路王木犊”了。
1982年,西铁分局相中了这个人才,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将王宪民从宝鸡调至西安,在分局工会当宣教指导员。这就给王宪民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舞台。1988年以后,王宪民主攻小品。第一次主演《大米与红高梁》不仅获了奖,而且收入了录像带出版发行。几年来,王宪民先后29次在陕西省和全国举办的小品大赛中获奖,并获省最佳演员称号。省、市、中央电视台新举办的各种文艺晚会中都有他精彩的表演。
王宪民不仅热爱艺术,而且积极上进,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优秀工作者。1984年他调到西铁装卸机械厂后光荣入党,任党办宣传室主任。
王宪民两次下乡当家民,又在秦岭大山中当修路工人,无论什么样艰苦的环境,都没有磨蚀他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踏平坎坷成大道,他终于跨入了陕西省职工艺术家的行列。对此,王宪民只说了一句话:“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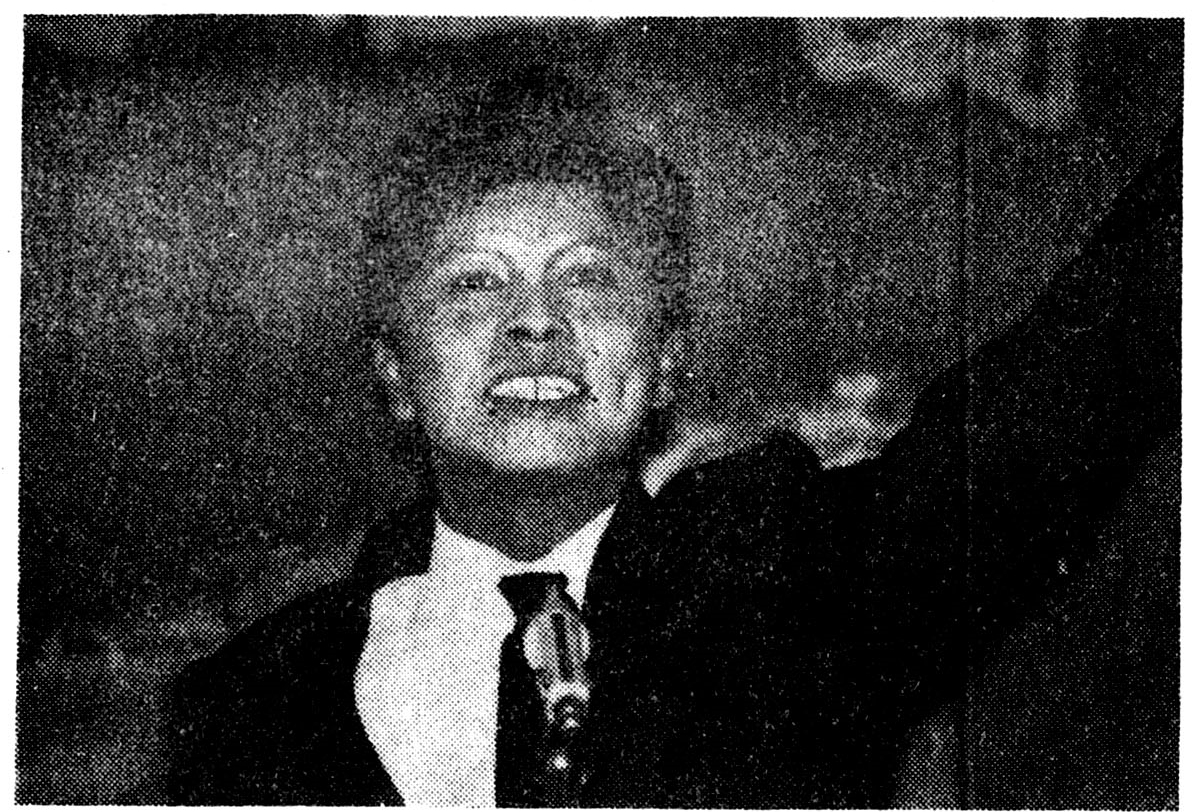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