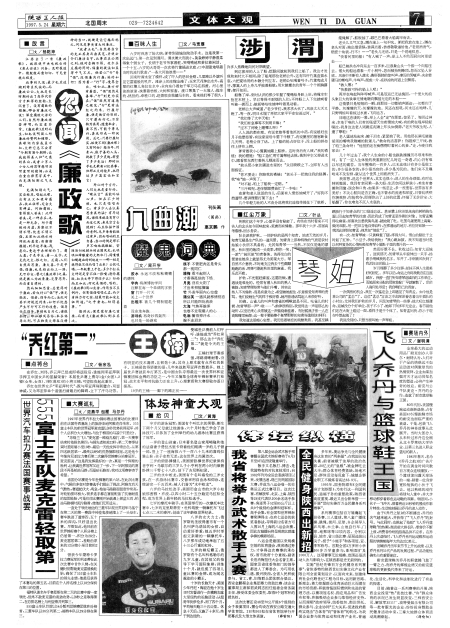
涉渭
文/马宽厚
六岁时我患了场大病,爹带到省城住院动手术。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见到渭河。渭水滩大而流小,袅袅婷婷平静温柔得象个弱女子。长胡子老爷爷掌着舵,笑嗬嗬地和爹拉着闲话。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哥哥一次次将竹篙插进水底,口中甜甜地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
回来时渭水变了模样,成了吓人的怒目金刚,几里路以外就听见它雷霆般的吼声。滩涂上的庄稼全淹了,玉米天花伸出水外,高粱的红穗儿耷拉在水中,全向东仆着如千军万马在泅渡。河心里浊浪滚滚,挟裹着枋板、大树和家畜。渡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推车的,挑担的,牵牲口的,赶着胶皮轱辘马车的。看来他们等了很久,许多人焦躁地向河对岸眺望。
到达彼岸的人上了船,眨眼间就轮到我们上船了。我这才发现和来时大不相同:除了船尾那位老梢公外,还有四杆竹篙直插水底,六把夏场用的木锨分列左右。老梢公吆喝着号子;竹篙弯成月牙,撑篙人的上身几乎挨着船舷;用木锨攉水的青年一个个袒胸露臂,挥汗如雨。
船靠了岸,来时认识的那少年握了缆绳纵身跃上岸,将绳牢牢拴在木桩上。早已等得不耐烦的人们,不待船上人下完就喊着叫着一拥而上,舷板咯吱吱地呻吟着晃动着。
老梢公大声喊道:“老少爷们,我求求大伙了,风浪太大天又晚了,等一夜,明日水塌了再把大家平平安安送过河。”
“我们等了大半天啦!”
“我们有急事等不到明日嘛!”
“过不了河晚上睡哪儿呀?”
人人说的都在理。有说老娘等着他抓的中药,有说媳妇坐月子他要经管,有说家里母牛要下牛犊了,有说圈里的猪崽断食几天咧。老梢公没了话。上了船的抢占好位子,没上船的拼命往上挤往上拥。
爹背着我小心翼翼地踏上舷桥。这时身后有人喊:“我的褡裢!我的褡裢!”船工急忙用竹篙帮他去挑,挑到半空又掉进水中,眼看那东西打着转儿顺流而去。
“前头那小家伙踢进水里的!”众目睽睽之下,立即有人出面指证。
“你不要走!你赔我的褡裢!”老头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我“哇”地一声哭了。
“对不起,咱上了船我一定赔。”
“三斤线呢,老伴熬眼费油忙了一冬哇!”
在爹和老人说话的当儿,后面有人愤怒地喊开了:“好狗不挡道呀,要讲理要打架下去!”
几个年轻力壮的人不由分说将我们连推带搡扯下了舷桥。
缆绳解了,舷板抽了,眼巴巴看着大船离岸而去。
老头儿又气又急,蹲在地上一句不吭。爹把我放在地上,蹲在老头对面,掏出烟袋锅,装满点着,恭恭敬敬递给他:“老哥消消气,赔您十块钱,行不?……”老头儿无语,只是一个劲地叹息。
“快看河里的船!”有人喊了一声,岸上人不约而同向河里望去——
船已被洪水冲向东去一百多米,巨浪象山头一个接一个向船压去。偌大的船远看象一片小树叶,忽而被抬到峰顶,忽而又坠人谷底。风浪中不断有人落水,撕肝裂肺的惊叫声,凄厉的哭嚎声,夹杂着骡马的嘶鸣声、牛哞声,混成一片,在秋凉的河道上空飘荡。
“救人哪!”
“快救救可怜的船上人吧!”
两岸也响起阵阵呼喊声,可是厄运已无法挽回,一个更大的浪头象巨大的铁拳无情地砸向飘摇无定的木船…
这情景只是短短的一瞬,刹那间一切都销声匿迹,一切都归于平静。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地。风还在怒吼,河水还在咆哮,几只野鸭惊叫着掠过水面,飞向远方。
目睹这悲凄的二幕,岸上人全“定”在那里,惊呆了。等回过神来,幸免于难的人们有的张望天空疾愤地大喊,有的爬在堤岸轻轻啜泣,我身边这老人则跪在泥滩上叩头如倒蒜:“老天爷收生呢,人遭了孽啦!”
老人猛地站起来,擦干泪水,紧紧抱了我。用他那长满毛碴碴胡须的嘴啃我稚嫩的脸蛋儿:“救命的活菩萨!你蹬掉三斤线,救了咱三条命呀!”他拍拍还在痴愣愣盯着河心的爹,“走,今晚住我家去!”
几十年过去了,我个人生命的小船也跌跌撞撞历尽艰难和坎坷。有了一定人生体验的我重新回忆儿时这一奇遇,内心仍有难以尽述的痛苦。当年罹难的一百多人,已无法统计有多少是做工的,多少是务农的;多少是当官的,多少是为民的。他们来不及嘱咐来不及安排,就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我常想,说这个世界大,其实也很小;说人的生命顽强,有时也特别脆弱。我仍有幸同乘一条大船,生活空间这样狭小,难免有磨擦和顶撞,误会和口角,如果多一些忍让,多一些宽容,世界该有多美好!不关心航向是否正确,也不管水的流速和深度,只管乱哄哄你拥我挤,你抢我夺,即便你占了上好的位置,怀揣了无价珍宝,大船翻了,你也难免不沉入水底的。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