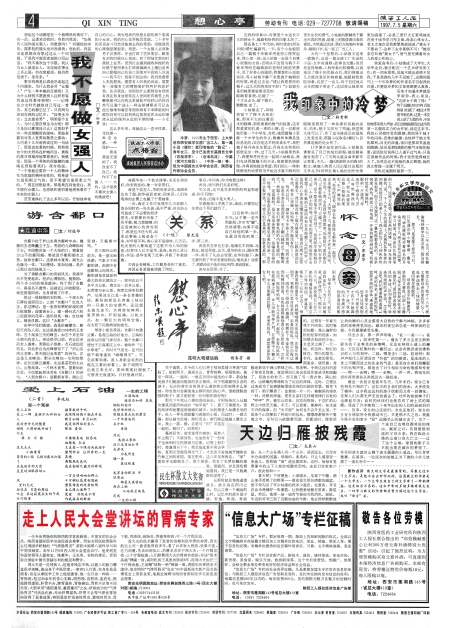天边归雁披残霞
文/龙泰山
关于离歌,古今的人们已将它唱得柔情万种荡气回肠了。皎皎明月、漠漠关山、青青杨柳、短短牧笛,甚至一阵风,一滴雨,一根在风雨中摇曳的小草,都会触发游子们敏感而脆弱的思乡情结。对于唱离歌唱乡音的游子,无沦你将生命悟得多么透彻将尘世阅得多么深刻,你也绝对会凝重地去倾听他们的心声。谁能摆脱故园的影子?谁又能轻视一份对根的眷恋呢?
那天下午我从六楼的房间走出,夕阳恰恰沉入从城市建筑顶面所构成的“地平线”下。遗下万缕霞光,宽容而详和地覆盖着嵯峨的城市,如抚摸爱人如瀑长发的手,给人一种充满温馨与感激的心绪。而这时,一群大雁,却从城市此端,绰约而去,渐行渐远地融入霞光之中。我心一震:雁,总是与“归”字连在一起的。雁归了,而我呢?
蓦然回首,竟发觉背井离家,居然八年之期了!不禁讶然。也油然有了一份对于生命和时空的困惑与空落。记得上初中时,每逢周日下午,我总拖延着不肯去学校。直到父母催促得生气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掩映在竹林之间的家园。现在想来,这八年东奔西走,“家”竟似乎无暇顾及了。那个黄昏,我有了长梦初醒的感觉。很强烈。并且很怅惘地感到:我已是一只脱离根的浮萍了。
从那时起总每每遥望故乡。故乡远在四川之北,巴山之南一个偏远的山村。记忆中的故乡是宁静、安逸、和谐、秀丽的。记得有一年春天我于外回家,其时春雨初歇,漫山遍野的松柏经春雨洗涤,如同翠衣初浣的少女,水灵灵立满了一天一地。而这时,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李花、金黄的菜花,围屋舍、绕田廓,秀雅地嵌饰于满山翠绿之间。那美啊,令我这远归的游子惊奇且惊喜。竟觉得自己来这里是作客或寻胜探幽了。而故乡的秋天,却又换了另一袭衣饰:满山松柏,由娇嫩的翠绿转为了沉沉的深绿。这时,它便反过来成为了如锦缎般围绕其身的田园的背景。稻花飞扬了,稻子飘香了,金黄地一片一片,被幽深的绿色一衬,优雅而深邃。更有乡亲们在拌桶里摔打谷粒的“呼呼”声,被空山回音,沉实而悠扬,于空旷的山野之中恍若天籁。冬天,可以看雾。雾静时,如水波不兴的海面,但“水平面”如何也不会升至山顶。于是各个山顶便如了传说中的仙岛,缥缥渺渺散布于雾海之中。足勾引人欲踏雾而游。而雾动时,便若洪波,从一个山谷涌入另一个山谷,滔滔远去。它没有半分洪波的凶猛,绵绵的,柔柔的,只让人渴望变一条鱼儿,悠然随“浪”迸出雾面来。这时,每每有笼罩雾中的山下人家的鸡骤然而鸣,由此引发家家户户,彼此相和……
夏天呢?下河摸鱼、小溪嬉水、瓜架下午睡、满山地寻觅熟了的野果……夏夜星空那份清澈的幽蓝,更不知勾引了年少灿漫的我多少遐思。在夏夜,爷爷总会为我铺好一张蒲篮,让我惬意地躺在里面,数星星。然后,他便一扇一扇有节奏地为我消热、驱蚊。年迈的爷爷已到了沉默如金的年龄,他总那样默默地让我幼嫩的心灵去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神秘。许多客居的夜晚停笔而出,城市的夜空却总是一种浑浊的空蒙,令我屡屡感受失落。
怀念乡音。那一声声呼唤:“爸——爸——;爸——爸——;回来吃饭——。”蕴含了多少尘世正渐渐驿失的千金难觅的亲情啊。无论在林间小道上的邂逅,无论在赶集时的一擦而过,总会有熟识或仿佛熟识的人与你招呼:二娃,哪里去?二娃,赶场呀?那声声现代人所谓没有“价值”的问候里,是浓浓的人世上可概而述之的生命的气息!甚至在乡亲们扬鞭驱牛的吆喝声里,都饱含了对牛相依为命的情感和怜爱——嘿——走啊;嘿——走啊,一声一声,将祖先的质朴淳厚善良从洪荒远古一路赶来。
最近一次回乡是前年冬天。几年未归,家乡已有些相见不相识了:记忆中的乡亲们的房舍,大多改变了模样,这令我这远归的游子欣慰而又有一丝惆怅;老辈人们大都无声无息的逝去了,壮年的叔叔婶子们也渐起华发;幼时的伙伴们也恍若有了润土式的隔膜;我成了许多晚我二十来年出生的人们的叔叔伯伯……。但幸,家乡的山还依旧,水也还依旧,家乡的乡音乡情依然令我感动不已。只是那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告别家乡“回”远隔关山的城市去了。为了一个连自己也难自圆其说的理由。离家之日,告别殷殷相送的父母乡亲,我在临近公路的山坳口良久伫立——过了这个山坳,家园的影子又只能出现在城市的梦里了。爷爷的故乡就在山脚下流水潺潺的小溪边,早已芳草萋萋。在溪旁,一位浣衣的姑娘正为下游的小伙儿放漂了一条红纱巾……
新作点评散文的文字是最要紧的。写散文过不了文字关,是绝不会出好作品的。这篇散文的作者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使自己的文字有了一种韵律感,这是相当不易的,这和平常的多读多练有很大关系。一切学习散文的作者都应努力闯过这个文字关,或曰“语言”关。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