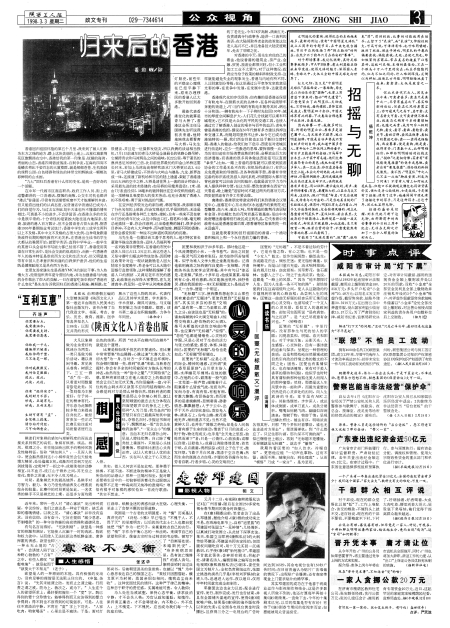
本版导读
心灵的响乐
——匡燮《无标题散文》漫评
田涧菁
匡燮和我相识于20多年前,那时他还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小伙,一身书卷气,谈吐之间显出一股灵气而又略有张狂;却为创作所苦恼烦难,似乎为难入文学大雅之堂奥而焦虑;记得他临别商洛之际我曾作自度曲一支相赠,并请商洛书法名家李志贤挥毫,其中有句日“姜还是,老来辣。”果然,十多年后,他成果累累,每每别有心会,别有意韵,而又能独出机杼,独抒性灵,摆在我面前的一本《无标题散文》,是他近年的又一力作,便是一个明证。
“无标题”三字,使我骤然想起李义山那些别有意会的“无题诗”,更使我想到“无标题音乐”,其实贝多芬的那些“交响曲”,虽有第一,第二乃至第五、第九之分,应该说也是“无标题”的,诸如海顿的《G大调交响曲》、《惊愕交响曲》,舒伯特的《C大调》,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等等,也应算作“无标题”,“惊愕”、“悲怆”也都是情绪性、心灵性的字眼。只是心灵对于生命的活力与张力的感觉、感受、体察、体验而已;匡燮的“无标题”,恰恰也是如此,“无标题”即标题也。
匡燮的“无标题”,应是心灵的际会,精神的通感,正所谓“美人香草屈原辞”;山川草木皆入眼,水泽幽花尽缠绵;在他的眼中,在他的心中,鼓荡着一股气韵一支芜笛一排芦管;碰撞着什么阻塞着什么皆成气流,发而为声,发而为音,有高有低,有粗有细,有激亢慷慨,有昂扬奋发,然而更多的是委婉幽绵,悲恻凄清,渺渺情思,飘飘臆想;入乎于云中,出乎于天外;似羽化登仙,类狡兔入林;清泉石上,鸟鸣山幽,黄花落地无声,细雨湿衣不见;当然不是黄钟大吕,也并非广陵散之绝响;却是食人间烟火者有感于生命的脉动,情衷于日月的流逝,心附于物,物化而成文;也非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者;只是一己情怀,心曲独奏;或聊以自慰,以慰他人;或藉以消除缕缕思绪,着笔于纸,点点滴滴,涓涓淙淙;或目之于色于光,激发怀想,飞着于月白风清,荡漾于空谷苍鹰;然而生命的斑斑点点自现,步履的苍苔露冷匆匆;劳者自歌,行者步唱,心灵的交响而已!
匡燮的“无标题”,不是不着边际的劳什子,它是有情之物,有心之物;也不是一些“小女人”散文,故作空闺闲愁,幽怨迭生;亦或踏花归去,惆怅茫迷;更无脂粉薄施,依待阑杆;而是山川崖石充溢,流水响林排闼;虽有眉月红袖,窈窕裙裾,闲草野花,佳石薇林,也都入之于心,附之于血肉浓浆;他说,这都是“一路上的风景。”因为“他不想探讨人生,因为人生是一条不可知的路”,却恰恰使我们在这高唱低吟之间,使人从这隐隐约约中窥视到作家的心路旅程;品尝到人生的况味;匡燮这一曲曲无标题的轻音乐所汇集而成的心灵交响;也谱写成了一个文人的心灵风景,看似文人的逸致闲情,却如司空图所说“是有真宰,与之沉浮”。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钟嵘语)
匡燮的“无标题”,字里行间,没有那种生与死的怕人的字眼;闪现着柔和、明媚、春天和阳光;对于宇宙万象,云影天光,人生感悟,心灵体验,自有一番诗意的追索与探求;呈现出一种哲理的美质;这是和那些纯自然景观或把自然引向政治抒情之类的散文的不同之处;固然,匡燮也有柔情似水,也有细语缠绵,更有对于美人香草的期待和切盼,他似乎也时时具有蒲松龄那种仙狐化美人而闯入的那种憧憬;然则,那都是这人生风景中的一部和声,而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向心灵深处的扣问,向人生真谛的寻觅;章节虽有ABC之分,其脉络憬然,步步深入,或总体或侧面,或单刀直入,或条分缕析,嘎嘎如惊鹤飞鸿,幽幽似深涧滴泉;情赋于物,物渗于情;呈现出鳞次栉比,皴法有序,明暗浓淡各得其所。只那“两个梦相对着攀谈,谁也无法走进对方里去”,便泄漏禅机;到“什么都忘了,只记住那片湖,那片深不可测的湖”,似已憬悟世上烟云,再到“无标题不是朦胧,无标题就是无标题”。就达乎“辙悟”。
我期待着匡燮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更想他应能“一切声色事物,过而不留,通而不滞,随缘自在,到处理成”,从而“顿悟”乃成“一家言”,是为至切。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