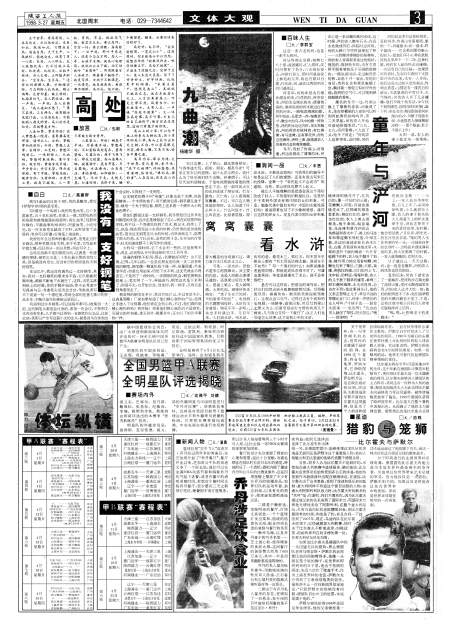
童年与浐河
文/李群宝
这是一条古老的河,也是一条不大的河。
河从终南山发源,宛转七八十里,流进灞河,汇入渭河。汉时河便有了名分,八水绕长安么,河排行第五。那时河是皇家上林苑的东界。附近有原日白鹿,曰乐游。河,就在这两原中间的川道流过。
河有床,河的床是丸石细沙混合的床,白花花的。河亦有水,河的水是刚出的水,清清亮亮的。清清亮亮的河水流过白花花的河床,一路唱着溅溅的歌。河中有鱼,长肥者一拃,细瘦者半寸,像空中的鸟,风中的旗一样欢势。河的积水处还有虾,呆头呆脑的。河的两岸有桃林湾,有红柳滩,有马连滩,还有蓼花洲。河的这些滩呀、洲呀上面,散落着农人的青砖瓦舍和蓑草庵棚。
冬天,雪封了终南山,河很瘦。河边沿都结了薄薄的冰,河中心是一条活蹦乱跳的水线。这时候,河的农人搬来石头,在浅水处做成列石,供临时过河用。河的大路口早些时就架起了桥——三四棵并排模卧的杨柳树。河的农人穿着新浆洗过的棉袄,挑担的,推独轮车的,也有空着两手跟着婆娘尻子后脚踏前脚的,一路说着闲话,走过颤悠悠的桥,去逛十月一庙会。在他们身后,青砖瓦舍和蓑草庵棚上空,飘浮着一绺轻云似的早炊的烟,清冽的空气中,可以嗅到燃烧稻根的香味。
漫长的冬天一过,终南山换上了黛紫的春装,河就涨了水。住在草棚屋的人夜里可以听到河起春汛的呜呜声。第二天早起,河的农人开始兴奋地拾掇农具,“六九、七九,沿河看柳;八九出了头,吆牛下河走!”河的农人这样传告。这时候,河的桃林湾的桃花开了,红的白的,像一片灿烂的云霞;花瓣飘入河里,河就流着桃花水了。红柳滩的柳条柔柔的,柳皮红红的,新叶也红红的。农人上滩去割柳条,挽牛鼻圈,编筐编笼。马连滩和蓼花洲的边角都浸到春水中了,滩上的马连草和蓼蓝脚长得旺盛,叶绿茎紫。水边的湿地还旺长着水红花、白蒿、苦苣苣和其他水草,水草的茎叶下面纠缠着一片片青蛙屙下的籽。农人吆牛翻开了稻地,格外用力地空甩着响鞭。响鞭也勾来了鹭丝、白鹤、天鹅、黄雁、燕抓拉的魂,它们在河上飞,水中钻,田畔巡,嘎嘎叫着。农人的儿子放下割草的镰笼,拿两三卵石满河滩撵,水鸟欢得很,总也打不到,他徒累满头汗。他的父亲正要喝止儿子,背后不远的草棚瓦舍门口,传来一声悠长的女人呼叫:“牛娃子也——跟你大回来——吃饭呀!”这边的男人就住了犁杖,回头答应:“噢——回来咧!”
河的最美季节是夏秋两季。夏秋两季,终南山爱落暴雨。暴雨一下,河就涨水;河一涨水,样子挺凶——它会教训那些粗心的农人,把他们不小心种在危险区的瓜果冲个一干二净。这种时候,河的农人就纷纷走出庵棚,一边巡看自己的庄稼,一边观望河的景致。还有的乍着胆下水捞取冲来的瓜果,水有一人多深,他们边凫水边探头望终南山。终南山真蓝,山腰还有一缕乳白的游云。不落暴雨的平常日子,天气燥热,河的农人多了几分慵懒,他们早晚干些零活,中午找个树荫困觉。困得没味的时候,就下河,坐在水里,精屁股挨着河床细白的沙,耳根子浸着水面,水就推着人缓缓朝前浮移——那个惬意,肚子不饿不上岸!
太阳一落,农人的妻子就拿来一领苇席,把晚饭也搬到打谷场上,一家人就着苇席吃饭。月儿上来了,凉风徐徐吹着,小儿就很快入睡。农人的妻子仰头给大儿指着天上的织女星牵牛星,讲叙老辈传下来的爱情故事。有时候,她会唱谣歌:“月亮爷,明光光,我在河里洗衣裳。”她的男人坐在苇席的另一头,一边抽着自种的生烟叶,一边喝着米酒或薄荷泡的茶。待大家都困了的时候,一家人就势睡倒,直到天亮。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河,也一直是老模样,河的农人的风俗也世代相沿。
直到后来,河的下游发达了一座城市,把河的沙石掏光修了高楼大厦,把河水圈进城里饮用。河的农人这才大吃一惊:他们的稻田进不了水,他们祖辈惯见的天鹅白鹤也不见了。于是,这些汉唐守苑士兵的后人常常在脱鞋涉河之后骂:
“喝,喝,让你喝老子的洗脚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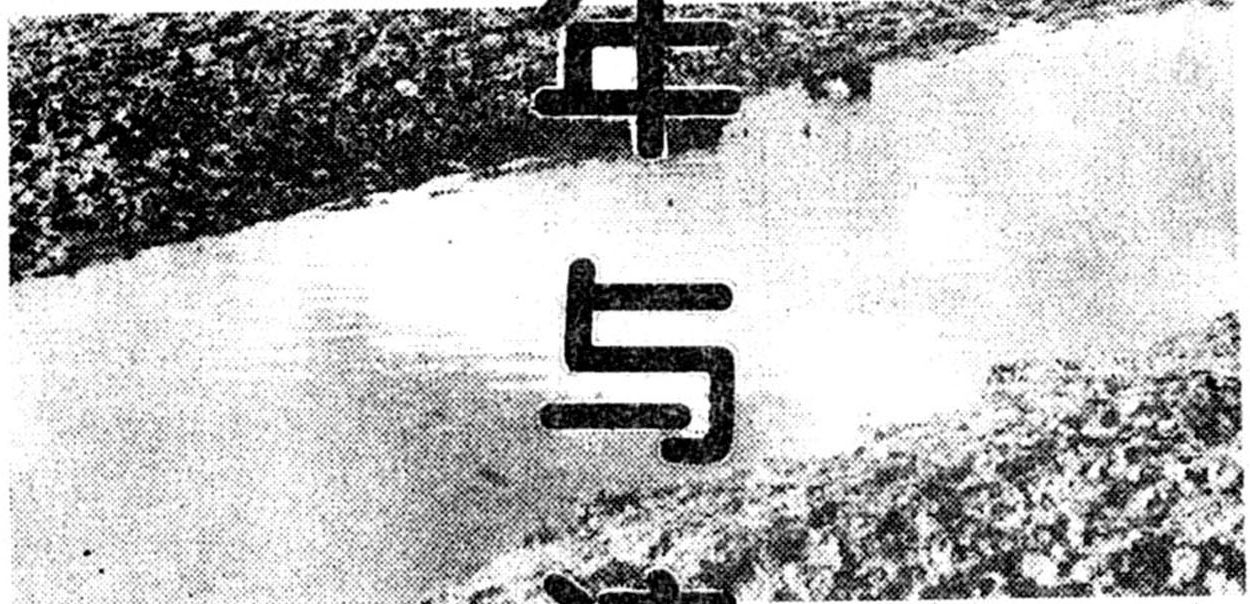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