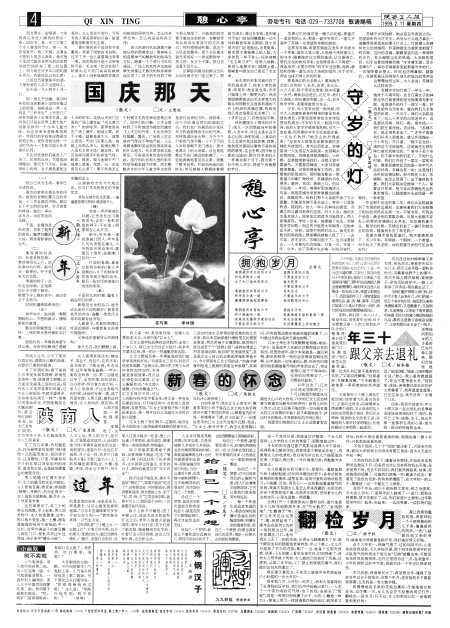
本版导读
守岁的灯(散文)
□文/管国颂
仿佛记忆的海洋里一艘不沉的船,那盏灯一直在我的心头,那是一盏守岁的灯,一座几乎是伴了苏姨一生希望和辛酸的航标。
这样写苏姨,希望苏姨能在虎年岁末成为一个形象,留在大家心里,大抵缘于传统意义上的守岁,随着城市化文明的推进,已日渐消亡;现代文化的缤纷多彩,也使得很多人不再把“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的守岁当回事。而我,曾经和苏姨一道生活在大杂院的居民,对于守岁,却总也抹不掉儿时的印象。
那是我们的大杂院么?整体敞开式的,没有院门,坐东、坐西、坐北五、六户人家,院子很深也很宽,院中间置一水井,南面自由进出。记忆中,我们大杂院人相处都很和睦,这一点,在年终守岁时,表现得就更为充分。
守岁,对小孩来说是一种欢娱,而对大人却意味着某种精神的象征和希望的寄托,尽管里面常常包含有传统惯性的成分。守岁的方式一般因户而异,有的人家守岁搞得很热闹,但不一定庄重;而苏姨的守岁方式却是庄重,一点也不热烈。“她怎么热烈得起来!”母亲在大院里各家都争着拉苏姨吃年夜饭时,常为此而叹息。苏姨孤身一人生活在大杂院里,坐西朝东住两间房。苏姨是很爱清静的。小时候,母亲就常教导我们,在院子里不要淘气,不要惹苏姨烦。大家对苏姨都很尊重。记得苏姨是有工作的,因着她的阶级成份,那时被发配在一家街道小印刷厂做校对。苏姨读的书也很多,唐诗、宋词、琅琅上口,但从不张扬,一年间,难得听到苏姨讲几句话,倒是苏姨对邻居常常露出的善良、典雅的笑,给我们那个大杂院平添了不少温馨。印象里苏姨不是本地人,常讲一口吴侬软语,轻轻的,给人一种小河解冻的感觉。苏姨之所以漂泊到我们这里,听大人说,她的先生是本地人,原来在江南读书与她同学,两人感情甚笃,学校一出来,她便随了先生。苏姨是有学问的,而且有可能是大家闺秀,但她命运不济。当初,战争打到我们这儿,她先生在教书回来的路上稀里糊涂就被人抓了丁,一去不返,杳无音信。苏姨泪流干了,也不说要回去,一人守着先生的祖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岁,成了苏姨对先生唯一的相思寄托。
苏姨守岁很独特,她总是在年夜饭之后,把屋里所有大灯关灭,然后从什么地方拿出一盏擦得雪亮雪亮的罩子灯点上。灯前摆上苏姨和先生的结婚照,怀里搂着先生被抓走前留下的衣物。这时的苏姨,眼睛里会闪出一种异样的光芒,有点超脱尘世的味道。大杂院的居民,似乎也都很理解苏姨“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每当苏姨屋里亮起那盏守岁的灯,一切喧哗都会停止,时间也仿佛凝固,隐隐的,苏姨那被压抑得很久很久的低沉的哭声也会嘤嘤地传过来。大人会说,苏姨怎么这样命苦!
苏姨守岁的灯亮了一年又一年,她终于不再年轻,往日江南女子的神韵也早已被爱情的坚贞拖累得无影无踪。流浪海外的归了一茬又一茬,好消息始终也没有来。就在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天中午,我们大杂院迎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白发老爷子,说是要找苏姨。我们一振:莫非他……我们赶忙接待他,告诉他,“苏姨不在,她去领养老金了。”老爷子看着我们好多人围着他,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开口道:“她不在也好,请把这个交给她吧。这是她先生那年阵亡前托我转交的。”老爷子丢下布包,扔下麻木的我们走了。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打开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布包,最里面赫然在目的是一块年代久远的怀表。苏姨也有一块!这是他们当年的定情信物。而今物在人去,苏姨啊,她怎么受得了!出于善良的本意,我们大杂院决定推举一个人,保管这只怀表,绝不告诉苏姨他先生的真实情况,让她隐隐中永远保留一种期待、一种希望。
作出那个决定的第二年,我们大杂院就接到了市里的拆迁通知,这意味着我们大杂院朝夕相处的居民将各居一方,不复为邻。听到这个消息,最悲伤的要数苏姨,尽管大家都不存私心的要把苏姨接过去养老,但苏姨执意不从。搬家的时候,苏姨径自拿了一盏灯和她先生的衣物,随福利车去了养老院。
看着苏姨手里的那盏灯,我不禁潸然泪下。多少年来,苏姨就一个期待、一个希望,而今她去了养老院,她的那盏守岁的灯还会亮起吗?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