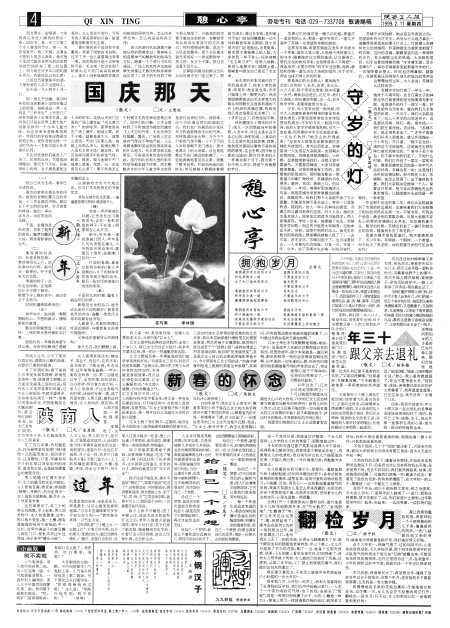
本版导读
年三十跟父亲去退礼(散文)
□文/胡冬梅
二十年前,父亲正担任我们大队得支部书记。当时,上面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社员出外打工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父亲对上级指示是从不打折扣的,他的口头禅是:“这是原则问题”。那时外出经商的人都会偷偷摸摸的,每到年关这些人总要送一些礼给父亲,希望父亲照应二下。因此每年到年三十,我家堂屋总堆满礼品,鱼、肉、糖、蛋等。不过我们姐妹三人是从不敢动一动的,我们深知这些东西都要被退回去。
那时,我们家一共八口人。祖母年迈,母亲常年生病,日子主要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和生产队分的口粮维持。连公社干部到我们家门口一站都惊讶:“你们家怎么住着草屋,哪一位大队书记家不是青砖红瓦的。”父亲自我解嘲:“住草屋好,冬暖夏凉嘛。”个中酸痛总被他那一串串爽朗的笑声遮住。
父亲每年三十晚上都匆忙赶回家,他带着大队通讯员老王,父亲叫过母亲,问清哪样东西是哪个送的,又让母亲把各人送的东西用袋子装好。然后兵分两种。短途的全交给老王送,并嘱他到人家好好说明理由。长途的就由父亲和我一起送回。
坑坑洼洼的村路牵着父亲和我。夜色深沉,寒星密布似万家灯火,那天父亲手提一塑料袋粉丝,风撕着他脖子上的围巾,我双手插入棉衣袖筒,紧缩脖子,深怕风钻进怀中。一路上父亲讲了许多话,现在都忘记了。
当我们敲开那家人房门时,好半天才有人出来开门。开门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她见到父亲和我满脸堆笑,又是搬凳子,又是倒茶,又是寒喧,父亲坐下来笑着说明来意,那妇女执意不接退给她的礼品,最终还是被父亲婉言说服了。父亲和那妇女又坐了一阵子,还特地问那妇女的儿子是否已在外做工回来,那妇女怯怯地说:“还没回呢。’临走,父亲对那妇女说:“放心,我心里有数就是了,你也不要考虑太多。”回到家,妹妹,弟弟都已在红红的炉火旁睡着了。我再望望堂屋里,已空空如也,我只好再一次咽下口水。
后来,我到外地读书,年三十跟父亲一起去退礼的差事就由妹妹或弟弟担任了。现在,我早已工作,结婚、生子。但这件事一直郁积在我的心里,成为我一部分的性格和生命。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