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艺谋答军艺学生问
文/图 余彦隆
从柏林电影节到东京电影节,从威尼斯电影节到嘎呐电影节,人们不断地可以看到张艺谋那熟悉的身影。近20年来,张艺谋无疑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前不久,张艺谋应邀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艺术创作的有关问题与军艺学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笔者撷取部分精彩答问,与广大读者共享——
▲问:《红高梁》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后来你的许多电影都是源于文学作品,请你谈谈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张艺谋:文艺创作首先要关注入。只有文学的繁荣,才有其它艺术门类的繁荣。尤其是电影,它直接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好的题材,好的故事。所以我说电影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影离不开文学。我搞电影至今一直是在改编文学作品。我可能是全国订文学期刊最多的一个,几乎每晚捧读至深夜。所以有作家惊叹说中国现在只有一个人在读小说,那就是张艺谋。实际上文学并不是搞创作人的事,全民族都应关注。如果我们老百姓的文学素质都提高了的话,我们的文学作品质量会更高,甚至刑事犯都会减少。
▲问:你的片子大都取材于农村,以后你能否拍一部解放军题材的影片?
张艺谋:我最早做摄影师,拍过一个《大阅兵》,是《黄土地》之后拍的第二部,后来就没涉及军队题材了。这么说吧,我肯定有兴趣拍解放军题材的,但是实话实说解放军题材的我们不愿碰。为什么?审查太严了。因为搞艺术的要弘扬人物个性,讲些关于人性的故事,不满足于作宣传。所以,有两类题材我们一般不去碰,一类是解放军题材,一类是少数民族题材,太敏感了。一般有点敬而远之。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拍一部非常好的军队题材的电影。
▲问:随着中美WTO协议的签订,以后每年将有30部美国大片进入中国市场,你作为一名电影导演有什么想法?
张艺谋:听说美国进口片不止30部,是50部。听说有两年的保护期。美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它就像NBA篮球一样,势力非常大,已培养出几代电影观众对它的迷恋。美国电影控制和影响着全世界的市场,所以我们常常说好莱坞是个狼,搞不好狼就来了。尽管中国有两年的保护期,但市场还是要慢慢开放,短时期内估计会对中国电影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因为现在每年只有10部引进,将来会更多,而且美国人雄心勃勃地想控制我们的电影院线。WTO谈判相当部分是关于这个问题。因为娱乐业的输出占美国输出第二位(第一位是波音公司),它的输出非常厉害,它赚全世界人的钱。我不想看到中国像周边国家那样一度被压得喘不过气。我们如果完全靠市场来调节,那就完了。我相信政府会在这个过渡期有得力的保护措施。
▲问:你的作品大都是文学作品改编的,我想知道你选择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你在选择演员时,是根据演员的形象来确定选择标准,还是根据演员的不同特点来改变你心目中的形象,你以为演员的哪些素质是你所看重的?另外,你是否在军校作过这样的讲座,你面对这么多军校生在台上有什么感觉?
张艺谋:我自己其实没有明确的拍片规划,我在选材时有意让自己自由一些,也不给自己定位拍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就像逛商场一样,不是特意要去买什么,看着好,就买了。我看小说很注重心动的感觉。比如:东北作家报时(音——作者注),名不见经传,他的小说《纪念》写得很平实,读来散文式的,我当时被一个细节打动了:主人公的老父亲是个老教师,上课回来很累,炕上一坐,经常是她妈去做好饭端上时,他爸在炕上睡着了……这个细节突然打动了我,就想拍。我自己看电影、看戏,也有这种心动的感觉。在某个高潮时,也突然心动一下,或者是突然掉泪,这是真正的心动,不是别的感觉。我觉得一部电影让观众在观看时,心动的感觉有一次,那么这部电影就成功了。如果有两次三次,那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我有两个原则,就是不重复。如果这篇小说感动了我,但与我过去某个电影的风格有重复,我会再考虑。至于选演员,我们不是明星制,很少度身而作。通常先搞剧本,然后再选演员。过去我曾跟巩俐合作时间较长,所以我也不忌讳(笑)。差不多合作两三部戏之后,后面就一定要考虑巩俐能演。这在我是一个过程。现在主要是看角色,怎么靠近角色,不是以个人的喜好,又不是找对象。所以要从各个角度出发去考虑角色才适当。
▲问:在第六代人拍的电影中,贾樟柯的《小武》很让人感动,但遗憾的是这是一部地下电影,你对此有何评价?
张艺谋:《小武》我看过,还不错。所谓地下电影就是未经审查的私制电影,全世界拍这种影片的很多,大都带有探索性。电影100年的历史,最初的发明是从一个杂耍开始的。它本身的要求是故事,要让人愿意看。但是如果一味地抱怨、逃避现实拍这种电影,等于放弃了与观众交流的机会。因此,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必须学会适者生存。也就是说,在现在的国情下怎样走自己的路,拍出具有自己特点的电影,这实际上是锻炼了你的生存能力。
▲问:你在《我的父母亲》中启用了我们戏剧系学员郑昊与章子怡搭档饰男主角,请问通过合作,你对军艺学生有何看法和评价?
张艺谋:请郑昊出演《我的父母亲》中的男主角,是我第一次跟军艺合作。我觉得军艺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作风比较好,郑昊给我的感觉非常稳重刻苦,不像社会上其他演员有些不好的作风。从郑昊身上我感到军艺学员非常规矩、认真。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会来军艺选演员,但是希望领导支持,能放人就行了。
▲问:您在电影领域取得的光辉成就是令人惊叹的,我们想知道你是如何走向成功的?
张艺谋:其实,每个人都想成功噢!但我自己是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改变了我的命运,否则我不可能有今天。那时候我在工厂已干了7年工人,此前插队当了3年农民。我也觉得前途是一片灰暗的,那时我们家的成份不好,我父亲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军官,那时候给我们家定的性是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基本上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从小就很自卑。我过去不爱说话,沉默寡言。我就是这10年导演当的话多了,罗嗦了。我在工厂当工人,三班倒,夜班很辛苦,那时最大的理想是到工厂宣传科以工代干当个宣传干事,因为那时我会写字、会照像。粉碎“四人帮”后,到了78年就想通过考学来改变我的工人处境。考体院没考上,又考美院,还是没考上,就阴差阳错上了电影学院。是这个偶然的选择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我1982年毕业的时候,我还在想改行,因为我是学摄影的,当时分配我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我不想去,太远了。我想回陕西老家,我曾跟陕西画报社联系,做一个摄影记者,不拍电影了。后来,说起来就话长了……总之,成功之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脚踏实地,保持平常心是最重要的。从你踏入影坛开始,你的目光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黄土地,你是否这样认为,中国电影要真正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必须关注电影的民族性?
张艺谋:这是不言而喻的,一定要注重本民族的特点。但是,“越是民族的越具世界性”这句话在实际操作中有个度的问题。有些题材是我们本民族特别感兴趣的,并且拍的也很好,但是拿去他们又看不懂,比如前几年《凤凰琴》写民办教师转正,他们就不明白。他们不知道这有多么重要,不了解就无法沟通。所以,我们要关注人类的共同性。人类共同情感上进行开掘,这一点很重要。特别强调地区性。我们看外国电影或文学作品,打动你的不一定不是那个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都不是,而是那个人性的故事。是人的性格,人的精神,人的力量,即人的故事打动了你。所以,艺术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的,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问:一个女人越到后面经验越丰富,思想也很有深度,像好莱坞的一些中,年女演员就非常受到重视,而我们好像给中年女演员的戏很少,为什么?
张艺谋:当然,这肯定是不正常的。一个演员三四十岁后就没有什么好戏可演,这不正常。尤其是女演员,实际上30岁后是个非常好的成熟期,也可以塑造许多有深度的角色。相反18~20岁多数是靠形象和气质,更多的是靠偶像。但是中国不一样,也许中国老百姓都喜欢年轻漂亮的面孔。总之,上了岁数的演员演戏的机会确实比较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改变这种状况。我自己现在也用的年轻女演员。这或许与市场有关。
▲问:从你的艺术实践看,你能写会画,当过演员,干过摄影,导演也当得顶呱呱,请你谈谈你是怎样提高综合素质的?
张艺谋:我原来爱好摄影,我是从摄影改行的。因我是在特殊情况下破格录取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所以那时我就想如果摄影学不进去就转行学导演。所以,我后来转导演完全是一种实际性考虑。谈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俗话讲“艺多不压身”,应该学些专业以外的知识。所以,我除了导歌剧之外,也希望导舞剧,还想拍些音乐电视。其实综合素质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在于你的吸收,在于你的悟性。坦率地说,今天电影人大部分在脱离生活,包括我在内,我们已不可能过正常人的生问活。我这个脸改不了,走到哪儿都认识我,我怎么可能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严格地讲,我们应该作工人、农民、士兵,那么你的积累从哪来?我觉得在于心。我们尽管处在信息时代,只要用心你就能与生活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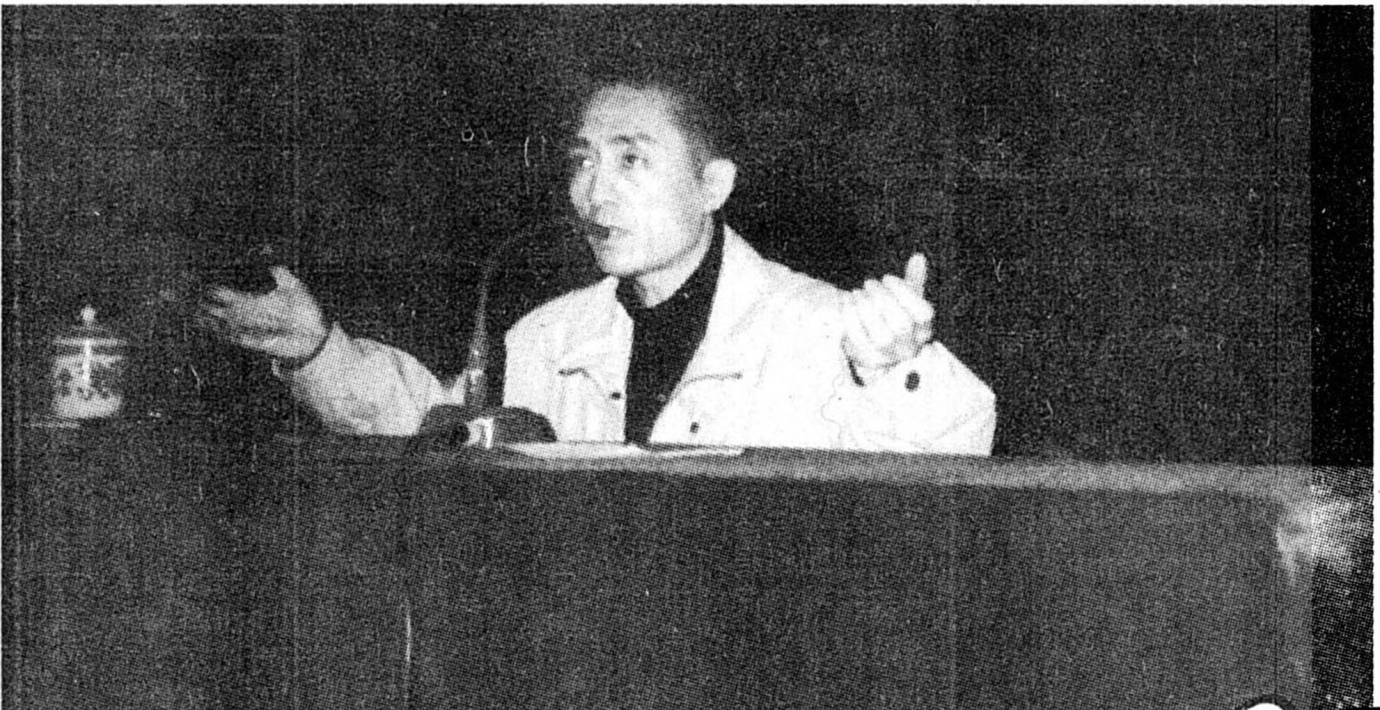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