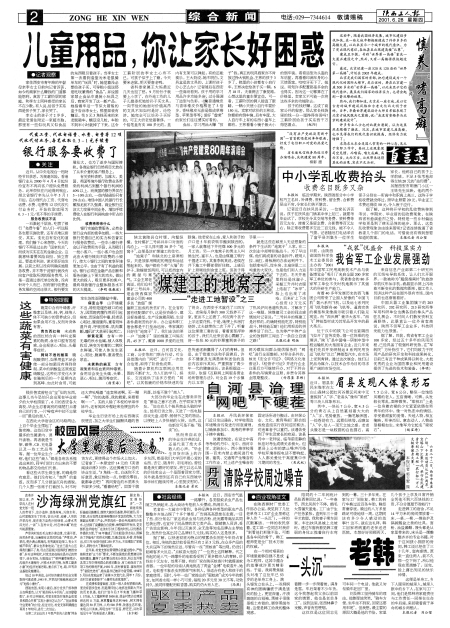
本版导读
“一头沉”老韩
在陕西铜材厂党委工作部办公室,我见到了几位老单身工(工矿企业里称这种人作“一头沉”),一样的沉默寡语,一样的农民穿着。党工部一位同志对我讲“别看他们形像不佳,可都是各车间的骨干,韩工程师更是全厂技术方面的权威。”
在一个相对艰苦的环境里能够自强不息成为工程师,这其中蕴含的故事或许更为精彩些。于是,我将聚焦镜头对准了这位年已53岁的老单身工身上。满头银发立在头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镶嵌于满是皱纹的脸上,更显深邃,汗渍斑斑的白短袖,黑裤子很像是粗土布做的,脚穿黑绒布鞋,这便是韩工给我的整体观感。
陪同的十二车间统计员张西林回忆说:“一年春节,西北风刮个不停,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工厂由于生产任务紧张,直到年三十清早才放假,我和妻子乘车回家,车出扶风县城上北坡时,透过车窗我看见韩工瘦弱的身体正推着自行车弯着腰一步一步爬着坡,满身是雪,车后架着不少年货,这令我想起我父亲以前回家的情景,他也是老单身工”。说到这里,张西林鼻子发酸,声音有些哽咽。
这仅仅是这位同志见到的一幕,三十多年来,在家与工厂间往复,韩工的自行车换过近百条车胎,鞋经常磨穿底,骑过的八万多里路足可绕地球一周,这期间该有多少令人感动的故事?!这不,就在这礼拜,韩工回家将病重的老伴送进医院,本想好好照顾两天,可车间一个电话,他就又匆匆骑车赶回厂里。
问及韩工坚持骑车的理由,他憨厚地笑笑,“骑车方便,坐车坐不到家,回家还要用车呢”。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他的节俭,家里几个孩子上学及日常开销全凭他不到六百块钱的工资,不分分厘厘节省能行?
走进韩工的宿舍,不足14平方米的房间摆放着一床、一桌、一椅、一煤油炉及锅碗瓢盆之类的灶具,面粉、油盐酱醋、馒头都是从家里带来的,床头是一撂整整齐齐的专业书籍。对于这间狭小拥挤的房间,韩工说已经住了三十几年,蛮有感情,原来一直住两人,前不久那一位下岗了,所以他现在更清静了。说完,脸上露出知足的快乐神情。
这便是单身工,乡下人眼里的城里人,城里人眼中的乡下人,在家与工厂间,他们是那种将家庭责任与工作责任一同架在生命的车后座,来回骑着疲于奔命的城乡两栖人。
本报记者 刘公望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