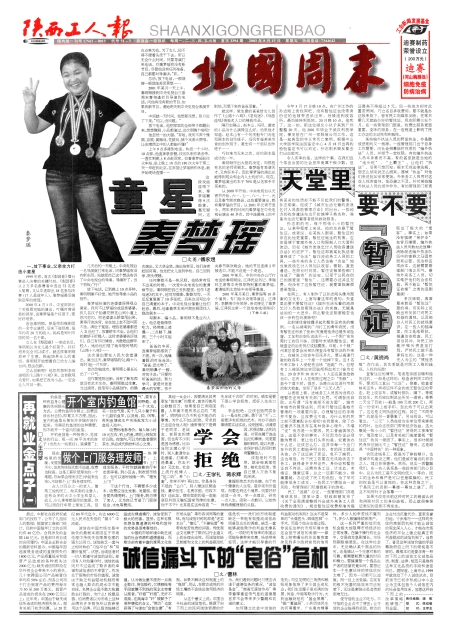诚信漏斗下的“良俗”危机
□文/曹林
最近,中新社在政府权威部门的授权下,公布了几组惊人的数据:据国家工商部门统计,目前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有40亿份,合同涉及的金额140亿元,但是却只有五成的合同履约:中国企业联合会的最新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假冒产品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缺失诚信同样给在华外资企业带来不小的损失,几十家跨国公司产品被冒仿率均有50%左右,而各公司用于打击假冒产品的费用每年为50至200万美元,假冒产品造成的损失在2000亿元以上;近年来,中国由于缺失诚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惊人,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共达6000亿元人民币在失信的“漏斗”中流逝。
诚信在中国市场交易中缺失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伦理中传统失信厚黑伦理的强大认同力,诚信缺乏一套与之相对称的“习俗平台”和“双赢价值观”。试想,当诚信者对一切人都遵守诚信的法则,却没有人对他遵守时,诚信的法则只不过造成了欺诈者的幸福和诚信者的不幸罢了。作为处于弱势的市场价值观,诚信由于缺乏利益驱动机制而常常也趟入欺诈的混水中不能自拔,名牌企业是不敢大张旗鼓去打假的,为什么?投鼠忌器,怕消费者以为市场上这种品牌有许多假货所以放弃使用这个品牌。所以假货能够泛滥成灾肆虐横行,诚信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显然,这种劣根性想依靠道德的呼唤和宣传的攻势是很难奏效的。
中国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诚信的社会资源和道德基础,而欺诈却有着丰富的厚黑文化底蕴。认为做生意不使用一点商业欺诈、背信毁约,欠债赖帐等手段就赚不到钱的观念主宰着从商者。“奸商”“奸商”,无奸不成商,在商海中“奸”被赋予了某种褒奖的含义,“欺诈”也就获得了与诸如“会做生意”、“有市场头脑”等形容词同等的意味。而与诚信对称的却是“老实本分”、“傻瓜”、“不善钻营”等带有挖苦性质的词语。传统商业文化赋予了欺诈以行业道义上的合理合法性,而诚信却缺乏制度和文化上的利益驱动机制。如果不解决这种制度上的“瓶颈”,那么,在欺诈成性的市场土壤绝不会结出信用经济的硕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今社会的诚信危机,根源于自下而上的民间诚信资源的价值危机——我们的市场制度缺乏一种能有效推动诚信品质普及众生的诱惑,缺乏一套能够战胜欺诈的利益支撑系统。一项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必须能给善带来实惠,给恶带来惩罚,这样才能引导善的行为。我们遇到问题时习惯去诉诸于道德信条的感召,“诚信是金”、“商海无涯信作舟”等带着厚重宣传气息的道德箴言并不会带来多少警醒和劝诫的意义。
如何建立社会中诚信的利益驱动机制呢?这决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小手术,而是个综合治理过程。你说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谁还会坚守诚信的美德——媒体上经常曝光的非法集资案涉及到多少政府官员的信用危机;司空见惯的三角债和赖帐现象拖垮了多少国企或私企;我们生活圈子里充满的仿冒、伪造、作假等欺诈行为:大到金融财经的“基金黑幕”、“银广夏骗局”、小到百姓民生的河南毒米、广东瘦肉精事件,多少人的辛苦钱不翼而飞,多少人被骗得倾家荡产。
这一系列严重的信用危机会极大地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在骗子横行的社会中,交易成本急剧增长,市场预期极端混乱。在这种社会中,无论确认某个商品的伪劣,还是确认一个生意对象的可靠,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搞清楚一个商品生产者的信誉究竟如何,要想证实一个生意伙伴的资信状况太难了,因为一切都可以造假。而一旦上当受骗,在现有的极不完善的低效率司法制度下,无论是索赔还是追债都困难无比。
使守信的企业不吃亏,不守信的企业占不了便宜;让守信的企业能得到奖励,欺诈的企业付出沉重代价,直至名誉扫地,寸步难行——这样的失信约束惩罚机制才能让诚信的观念深入人心,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平台上建立起真正有利益驱动的诚信机制了。当然了,普及这种诚信价值的手段靠政府自上而下的俯视是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孕育一种自下而上的诚信文化诚信品质,制度、法律、规范只是维持这种文化品质的手段和途径而已。据报道,上海市从1999年就启动了个人诚信试点,目前该市已初步形成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包括个人诚信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但愿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策略能够推广到全国。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