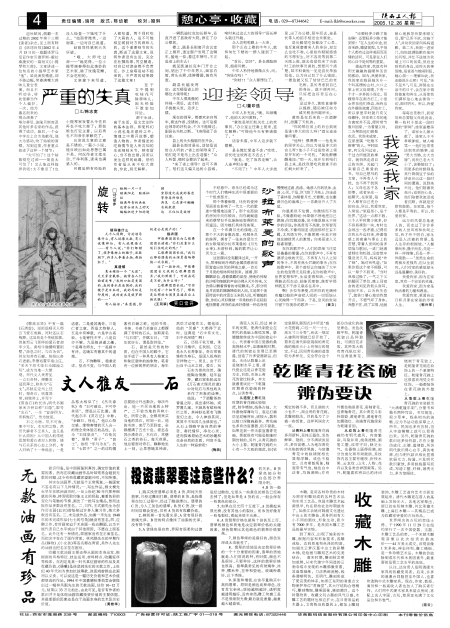
文人雅友——石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石清虚》,说的是顺天人邢云飞爱石成癖,死时还以石殉葬。这虽然是个传统故事,但象邢云飞那样的爱石者却非少见。唐相牛僧孺特置别墅,“游息之时,与石为伍”,其友知其有石癖,纷纷以奇石进献;李德裕置平泉山庄,“采天下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成为当地一大景观。宋代文人来芾见一立石奇特,便整衣冠而拜之,称其为“石丈”;苏轼在定州上任时,得奇石,欣喜异常,刻铭其上,并写下《雪浪石》的长诗;明代书画家米万钟自称“石隐”,取号“友石”,一生“宦游四方,所积惟石”,传为佳话。
石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本无用之物,然历代癖者不乏其人,这又是什么原因?从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和爱石者对人和物、情与石关系的心态上分析,有人归纳了十一种说法:一是适意,二是爱其瑰奇,三是仁者之意,四是尤物移人,五是中有禅意,六是学古高致,七是寄托不平,八是自亦不解,九是极游遨之趣,十是尊为师友,十一是画中有诗。这确实有着其中的道理。
石,不饰雕琢,稳重安详,坚贞不变,与中国人的品格太相似了!《吕氏春秋》有“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便是以石比德。清代赵尔丰《灵石记》中称:“余癖石,性也。”他以心物交感、缘物寄情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来体验石的品性,认为“石体坚贞”、“石性沉着”,堪称“君子”、“良士”,故而“乐与为友”。抗日“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素有石癖之称,他的书房、书架、书桌乃至窗台上都摆满了奇特的石头,故取斋名“与石居”,并赋石曰:“吾生犹好石,谓是取其坚。”
石,固然是天然的物质,但在中国人的眼中,它似乎成了一种具有人格意义和象征意味的抽象物。笔者有一位新闻界的朋友,每年总要因公外出数次,每次外出,他一不买当地的土特产,二不尝当地的风味小吃,所带之钱,全都用来买当地的异石。时间一长,他的书房、客厅乃至卧室,全都摆满了五光十色、姿态各异沙漠奇石、木化石、灵壁石之类的奇石,每天夜里,他总要面对奇石,静静地坐上一刻,让思想随其神游,然后才动笔作文。据他说,他的“灵感”大都得于此时,这真是“石中有文化,石中有深情”啊!
石,历经千秋万载,承受日月精华,在我国,它还是永久长寿象征。奇石常被雅称为寿石,是国人祝寿的吉祥物之一。而且,由于石出自于山水之间,爱石、玩石实为崇尚自然,确能陶冶情操、延年益寿。藏石家张轮远在《万石斋大理灵岩谱》中对玩石与养性的关系作了形象的诠释。他说:“于酒酣茶热香温之际,或出诸怀袖,或罗置几案,不独具有缤纷绚烂之形,其神妙处更有飞腾变幻之态,令人神游其间,冥冥中不知其几生修到也。”从石上领略宇宙自然的神奇,寄托情怀,净化心灵,进而探索原始艺术的妙趣和生命自然的本质,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追求呢?
(梅浪)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