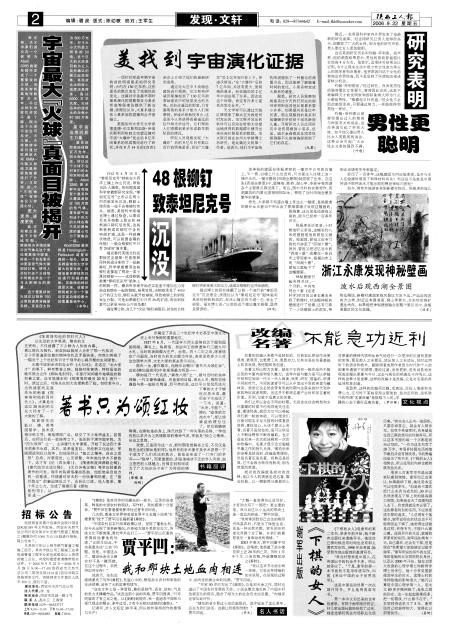
本版导读
著书只为颂红妆
《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以生动的文学笔调、翔实的文史资料,不仅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更以陈氏为契机,剥茧抽丝般深入分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所普遍面临着的精神危机及矛盾抉择,向我们再现了一幅关于上个世纪知识分子艰辛的心路历程的生动画卷。无意中读到余杰的处女作《火与冰》,在这位“北大怪才”的笔下,鲜有赞誉之辞。独独对陈寅恪,特别是他的晚年倾力之作《柳如是别传》,字里行间却意外地满是钦敬仰慕之意。还有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流行一时,读过之后,对陈先生的大名便熟悉了些。但时至今日,当我读罢刘克敌先生的新著《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才算是对这位20世纪的文化大师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陈寅恪先后赴日、德、美等国留学,虽未获得半纸文凭,倒是博闻广洽,结交了不少良师益友。回国后,在师友们的一致推荐之下,他任职于清华国学院,为“四大导师”之一,主讲唐代文学课程,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教书生涯。其后,虽多值变乱,历经新文化运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但他始终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持,冷眼观世,心无旁骛,牢牢抱住学术不曾放下,这才有《论〈再生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举足轻重的著作的问世。晚年的陈寅恪凄凉孤独,他拒绝来自官方的一切邀请,怀揣着对学术的一份执着和热爱,在“盲目膑足”的窘迫境况之下,由自己口述,他人笔录,集十年之心力,完成了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从而进一
步奠定了其在二十世纪学术史甚至中国文化史上无可争辩的重要地位。1927年6月,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葬礼上,陈寅恪、吴宓向王国维遗体行三跪九叩大礼,当时的场面颇为庄严、壮观。四十二年之后,陈寅恪在广州逝世,当时官方的反应颇为冷淡,甚至没有多少人对这位国学大师、文史大家的离去表示关注。陈氏一生,著作颇丰。他晚年自嘲曰“著书只为颂红妆”,这在《柳如是别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柳如是乃一代名妓,“秦淮八艳”之一,嫁与当时的东林领袖、一代文豪钱谦益。后值崇祯自缢、清兵入关,柳即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而可笑的是,这位平日侃侃而谈天下事的大才子顿时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道“水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让钱谦益给硬拉住了。然后钱腆颜降清。在柳如是的身上,陈氏找到了一种失落的品格,一种他孜孜以求并为之热情歌颂的精神气质,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想,正是因为这一点,新时期思想解冻之后,不仅仅是陈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他所有的学术著作及学术思想一下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还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陈学”。而更重要的,则是他峻洁不迁的学人风骨,独立苍茫的人格魅力,仿佛在刹那间成为了广大知识分子所广为传颂的榜样。
(郭梅潘 旭艳)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