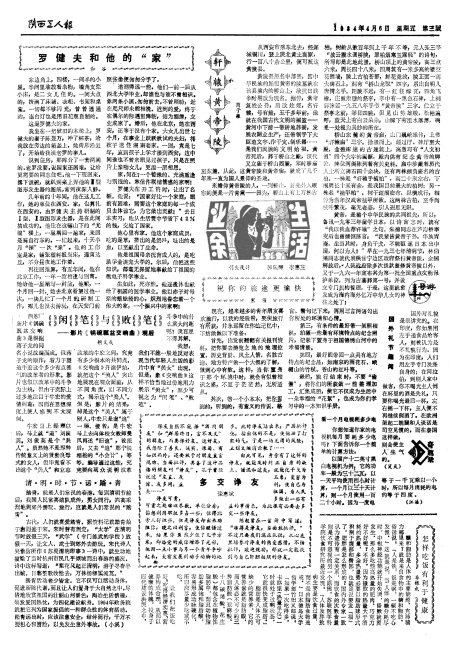
罗健夫和他的“家”
和谷
东边角上,四楼,一间半的小屋。半间里堆放着杂物,墙角支张小床,是二女儿住的。一间大点的,挤满了床铺、衣柜、书架和桌案。一切都不够闪光,普普通通的,连台灯也是用旧花瓶自制的。
这是罗健夫的家。
我坐在一把破旧的木椅上,罗健夫的妻子陈显万,冲了杯茶,给我放在旁边的箱盖上,她倚床沿坐了,开始给我谈老罗的事儿。
说到住房,那阵分了一套两间的。老罗没要,说国家还困难,让给更需要的同志住吧。他一下班回来,撂下饭碗,就趴到桌上弄他的Ⅰ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常到夜深入静。
几年前的十年间,他在这儿工作,她的单位在西安。家,也算扎在西安的。由罗健夫主持研制的Ⅰ型、Ⅰ型图形发生器,是在此间搞成功的。他住在这骊山下的“光棍”楼上,一星期回一趟家,来回是骑自行车的。一忙起来,十天半月“探”一次“亲”他的工作室是家,铺张塑料板当床,通宵达旦,不分昼夜地工作着。
再往回推算,有五年间,他在北京工作,一年一度相逢与别离。她给他一星期写一封信,他呢,一个月回一封。她去北京看望过他一次,一块儿忙了一个月的研制工作,哪儿也没去游玩,在天安门前照张像便匆匆分手了。
追溯得远一些。他们一前一后从西北大学毕业,却谁也与谁不曾相识。象两条小溪,匆匆前去,不曾顾盼,近在咫尺却未能相挽。迟到的爱,终于在偶尔的际遇里降临,结为姻缘,立业成家了。婚后,他在北京,她在西安,还等于没有个家。大女儿出世七个月,在事业上跃跃欲试的夫妇,将孩子送住湖南老家。一别,竟是七年,直到孩子上学才接到西安,这中间谁也不曾亲眼见过孩子。只是在照片上亲吻女儿,更添一层相思。
家,何在?一个特殊的、充满重逢与别恨的、靠信件联结情感的家啊!
罗健夫在升工资时,让出了名额。他说:“国家好比一个家庭,眼前有困难,需要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去体谅它,为它做出贡献!”去日本实习,他从生活费中节省下42%的钱,交给了国家。
他心里有家。他这个家庭成员,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汁,吐出的是血,以至献出了生命。
他是祖国母亲抚育成人的,是吃助学金读完大学的。尔后,他把这些知识,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微电子科学事业。
生如此,死亦然。他连遗体也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他以赤子对母亲的蜡烛般的心,炽烈地眷恋着一个伟大的家,一个振兴中的家啊!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