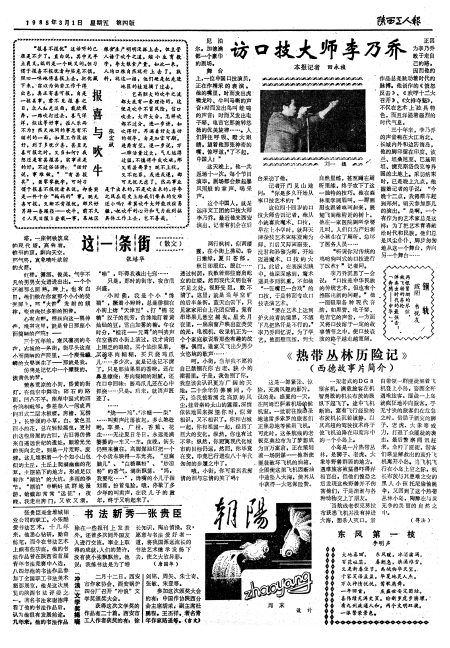
这一条街
(散文)
张培华
塔。一座钢铁筑成的现代塔,高耸着。锥形的顶,刺向天空。那气势,真象喷吐欲射的火箭。
红楼。潇洒、俊美、气宇不凡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一个个还都那么面熟。晚上,也有白日,他们映在你家那个小小的荧光屏上,那“火箭”发射的频律,变成绚烂多彩的图像。
心有点颤。情丝向这一隅伸牵。难道这里,就是昔日那座小而简陋的产院?——
三十五年前,寒风凛冽的冬夜,古城的一条街,街尽头这座小而简陋的产院里,一个瘦骨嶙鳞的女婴诞生了——那就是我。 仿佛是记忆中一个朦胧的、淡黄色的梦。
萧条荒凉的小街,昏黄的街灯,在低空中舞动;碎石的路面,凹凸不平。座座中国式的四合院相毗邻,参差杂入一间或两间旧式二层木板楼。房檐、瓦楞上,长脖颈的小草,白、紫色丑而小的花,总在轻轻摇曳,更衬出这些房屋的古旧,古旧得仿佛来自遥远世纪的遗址。顺着光光的街向北走,则是一片荒野、废墟。这儿堆积着一个个如小山包似的土丘,土丘上爬满幽幽的花草。土层陷下的地方,形成足以称作“湖泊”的大坑。多雨的季节,“湖泊”中蝌蚪成群地漫游,蛤蟆却常常“远征”:夜晚,我走出房门,又软又滑,“哇”,吓得我魂出七窍……
只是,那时的街市、夜市很兴盛。
小时候,我是个小“馋猫”,撅着小辫辫,总是徘徊在小街上烤“天津豆”、打“棉花糖”汉子的机旁,贪馋地盯着黄灿灿的豆,雪白如雾的糖。午夜时分,“桂花——元霄”的叫卖声在空落的小街上滚过,我才肯闭上困乏的眼睛。买个油炸果果,买碗枣肉糊糊,买只烧鸡爪儿……多少次,真是记也记不清了。只是那油果果的香味,还在鼻息缭绕;枣肉糊糊的甜腻,还在口中回味;酱鸡爪儿还在心中抓挠……只是,后来,就消声匿迹了。
“烧——鸡”、“冰糖——梨”……叫卖声此落彼起,多么熟稔哟。苹果、广柑、香蕉、花生……无论夏日冬日,永远是满篓篓的一车又一车。夜晚,街头仍熙来攘往。高脚煤油灯把一个个小货车映得一车光亮。 “豆腐脑儿”、“白糖藕粉”、“炒凉粉”的香气,满街飘荡。“妈,我要吃……”,馋嘴的小儿子指划着,扮着鬼脸。哦,停歇了多少年的叫卖声,在我儿子的童年,终于又响起来了。
两行枫树,似两缕霞,在小街上拂动。春日嫩绿,夏日苍郁,秋日却殷红、殷红……透过树荫,我数着那些磨肩屹立的红楼。然而现代文明也有不足之处,视野受阻,数不清了。这里,就是当年空旷的后半条街。蓝天白云下,只见家家阳台上花团似锦,竟有串串果儿悬空摇曳。星光月夜里,一扇扇窗户映出蓝荧荧的光,电视机、收录机正为一个个家庭叙说着那些有趣的故事。偶而,谁家又飞出少男少女悠婉的歌声……
呵,小街,当年我不愿将自己禁锢在你古老、狭小的裙裾里。于是,我告别了你。我应该去认识更为广阔的天地。二十余年仿佛瞬间,今天,当我披着渭北高原的风尘,挂着秦岭太山的露霜,深情依依地回来探望你时,似曾相识,又不相识了。你和古城一起,你和祖国一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纵然,你也有过不幸;纵然,你距离现代化城市的目标仍远,然而,你毕竟在变,毕竟已行进在八十年代匆匆的步履之中了。
哦,小街,你可看到我痴情的泪与忘情的笑了吗?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