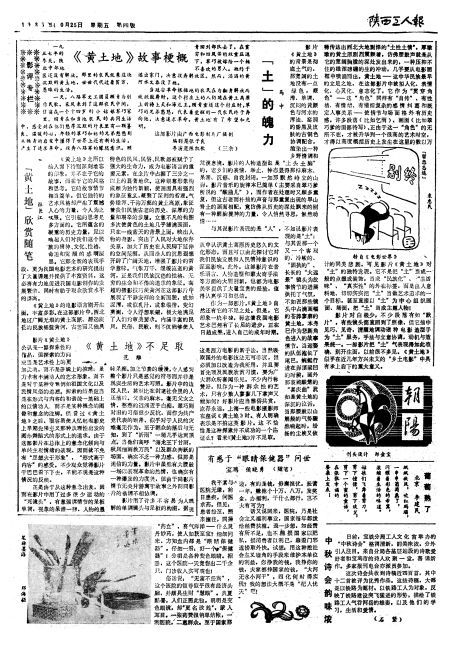
“土”的魄力
马中
影片《黄土地》的背景是彻底土气的,那宽阔的土地没有一点绿色,凝滞、单调、沉闷的黄颜色与河水的浑浊、窑洞的昏黑及皮肤的古铜色协调配合,渲染出一种乡野情调和荒漠意境。影片的人物造型也是“土头土脑”的,老乡们的表情、举止、神态显得那样麻木、呆滞、沉郁、自我封闭,一如那默然峙立的山峁。影片音乐的旋律本巳简单(主要采自翠巧爹所说的“酸曲儿”),而作者在处理时又颇多重复,但这古老而朴拙的声音与那重复出现的旱山脊土的画面相配,竟仿佛从历史的深处飘来的别有一种醒脑提神的力量,令人悄然寻思,愀然动情……
与其说影片表现的是“人”,不如说影片表现的是“土”;与其说那一个又一个客观的、冷竣的、“固执的”、长长的“大远景”镜头为故事情节的进展烘托了气氛,不如说那些镜头中占满画幅的苍莽寥廓的黄土地,本身已作为悲剧角色进入的故事情节。当迎娶的队伍拖长了尾巴,蜿蜓行进在峁顶梁凹的时候,画外那衷婉酸楚的“喜庆曲”犹如是黄土地的深沉的泣诉,当那腰鼓以山崩般的气势骤然响起时,纷扬的尘埃又依稀传达出西北大地剽悍的“土性土情”,厚墩墩的黄土原剧烈震颤着,仿佛腰鼓声就是从它的宽阔胸膛的深处发出来的,一种压抑不住的雄浑磅礴的生的冲动,几乎要从电影画框中喷涌而出。黄土地——这中华民族最早的立足之地,在这部影片中被拟人化、表情化、心灵化、意志化了,它作为“贯穿角色”——这“角色”同样有“自传”、有性格、有情绪、有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和既定人事关系——使情节与场面格外有历史感。许多段落(比如乞雨)、画面(比如翠巧爹的面部特写)、正由于这一“角色”的无所不在,才被升华到一个很高的艺术时空,才得以高度概括历史上发生在这里的数以万计的同类悲剧。可见影片《黄土地》对“土”的独特发现。它不是把“土”当成一般的点缀或装饰,当成“民族化”、“生活味”、“真实性”的外在标签,而是出人意料地、切切实实把“土”当做艺术追求的一个目标,甚至直接以“土”为中心组织画面、场面,把“土”当成主题人物!
影片对白极少,不少段落有如“默片”,有些镜头简直回到了照像,但它拙中见巧、见奇,清醒地调动诸种电影造型手为“土”服务,手法与立意协调,动机与效果统一。一部影片把“土”气表现得如此准确、别开生面,以前很不多见。《黄土地》似乎在近几年方兴未艾的“乡土电影”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意义。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