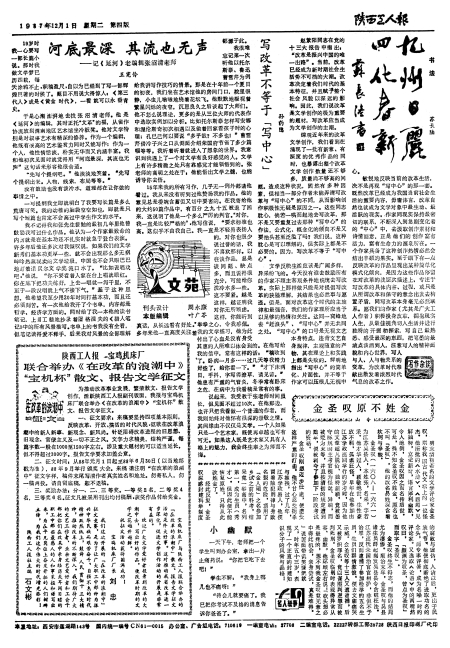
河底最深其流也无声
——记《延河》老编辑张沼清老师
王宪伶
19岁时我一心要写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做文学梦巳历四载,每天涂鸦不止,积稿盈尺,自以为已经到了写一部辉煌巨著的时候了。题目不用说大得惊人:《第三代人》或是《黄金时代》,一看就可以永垂青史。
于是心潮澎湃地去找张沼清老师。他是《延河》的编辑,其时正托“文革”的福,从省作协流放到渭南地区艺术馆坐冷板凳。他对文学特别是对叙事艺术有精深的修养。作为一个编辑,他既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同时又能写作;作为一个人,他性情恬淡,朴实无华而又内涵丰富。我和他初次见面时就觉得用“河底最深,其流也无声”这句话来形容他很合适。
“先写个提纲吧。”他淡淡地笑着。“先写个提纲出来。人物,线索,布局等等。”
没有鼓励也没有泼冷水,道理都在让你做的事情之中。
一写提纲我立即就明白了我要写长篇是多么荒唐可笑。我的幼稚的脑袋空空如也,即就是只写个短篇也肯定不会高过中学生作文的水平。
我不记得我和张先生接触的最初几年里他曾鼓励我写过什么作品。他认为一个作家最致命的内伤就是在基本功还不扎实时就急于登台表演。许多年后他还多次对我慨叹说,如果我们的文学新秀们基本功更厚一些,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无病呻吟热蒸现卖的文学垃圾。中国也不会只眼巴巴地盯着诺贝尔文学奖流口水了。“比如说唱戏吧。”他说,“你不要看着人家在台上唱就眼红。你在底下把功夫练好,上去一唱就一泻千里,不至于一段没唱就上气不接下气。”基于这种思想,他希望我至少用20年时间打基本功,而且还必须刻苦。有一次他给我开了个书单,内容都是哲学、经济学方面的。同时给了我一本他的读书笔记,上面工整地抄录着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所有风景描写。书单上的书我没有全看,但笔记读得爱不释手,后来我对风景的全部理解都源于此。
我很难忘记第一次听他以托尔斯泰、鲁迅曹雪芹为例给我讲写作技巧的情景。那是在十年前一个夏日的初夜,我们坐在艺术馆他的房间门口,院里很静,小虫儿嗡嗡地绕着花坛飞。他默默地凝视着繁星闪烁的夜空,沉思良久之后谈起了大师们。他不怎么说理论,更多的是从三位大师的代表作中选取实例加以分析。比如托尔斯泰怎样写安娜和渥伦斯奇初次相遇以及偷着回家看孩子时的心理;孔已己何以要说“多乎哉?不多也!”曹雪芹借冷子兴之口从侧面介绍荣国府节省了多少篇幅等等。我听着听着就进入了想象的世界。我意识到我遇上了一个对文学有良好感觉的人。文学上有许多精微之处只有靠感觉才能领悟到的。张老师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悟出文学之髓,也能诱导你去悟。
15年来我的所有习作,几乎无一例外都请他看过。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赞扬我的作品。他的意见总是委婉含蓄但又切中要害的。在我寄给他的大约50篇作品中,有百分之九十五被退了回来,这说明了他是一个多么严厉的判官。“对你,我一直是比较严格的”。他写信说,“要求标准也高。这似乎不由我自己。我一直是不轻易表扬人的,对你也很少说过誉的话,我不喜欢那样。以往谈作品,总是谈问题、缺点多,而且说得很充分,可能给你泼冷水多一些。这不要紧。越是这样,越证明我对你无所顾虑。这样,你能听到真话,从长远看有好处。”拳拳之心,令我感佩。多年来他一直高度关注着我的文学练习,他为此付出了心血是没有身受其惠的人所难以体会到的。在他写给我的信中,常有这样的话:“稿收到了。卧病一月多……过几天等我精力好些了,给你看一下。”“才下床两日,手抖,字写得潦草,请见谅。”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冬季常有卧床之危,在病中为我看稿是常有的事。
说起来,我受教于张老师时间虽长,但见面不超过10次。在他那边,也许只把我看做一个普通的作者,而我则始终对他怀有很深的崇敬之情。其间缘由不仅仅是文学。一个人如果只是一个艺术家,既使再卓越也可有可无。如果这人既是艺术家又具有人格上的魅力,我会终生奉之为师而不悔。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