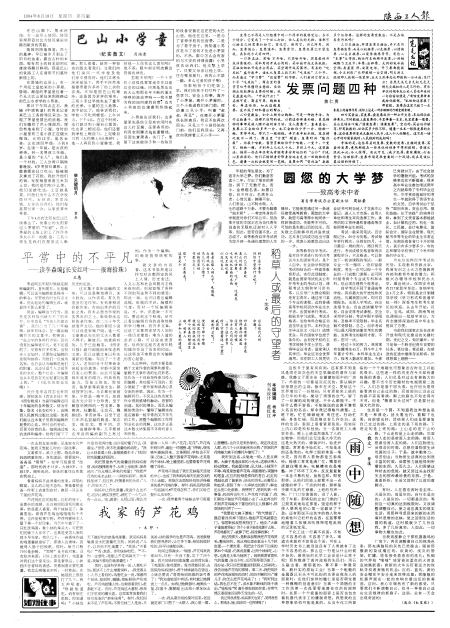巴山小学童
(纪实散文) 肖培清
在巴山脚下,黑水河傍,有一座烈士陵园,陵园里埋葬着32位为修筑襄渝铁路而献身的英躯。
陵园用围墙围着,烈士的墓碑,早已被岁月剥去了旧日的油漆,露出古朴的本质,唯有烈士的姓名却用红漆涂得醒目鲜明,那是巴山的铁路工人在清明节扫墓时新描上的。
在围墙的边沿上,有一个用泥土垒起来的小茅屋。昏暗、潮湿的茅屋里住着一个从大巴山深处来到铁路边的巴山乡求学的小男孩。
那日下午四点左右,我随《中原铁道》的两名记者来巴山工务指导区采访,发现了茅屋里冒出的炊烟,我们在瞻仰了烈士陵园后,便自然地来到了小屋。当时的小屋里有三名小孩正在烧火做饭。大的12岁,是名女孩,正在读四年级,小的8岁,在读一年级,是女孩的弟弟,另一名男孩三年级,是小屋的“主人”。他们是一个村的。三人分两口锅做着晚饭。8岁男孩叫谭林,正鼓着腮在灶口吹火,脸被烟灰熏成了花脸。我拉开他们的锅,发现锅里煮着玉米加土豆,我问他们吃什么菜,他们说就吃这,土豆就是菜。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学校搭伙吃。女孩说,家里没钱。女孩告诉我们,他们每星期回家一次,从家里背米带菜。
F午4点的太阳在巴山已快落山了,快落山的太阳穿过小茅屋的“天窗”,在小茅屋的土墙上印上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圆盘,三名小学生见我们在屋里这儿瞅瞅,那儿看看,就用一种惊奇的眼光看我们,当我们向他们询问一些学校及他们家中情况时,他们又将头深深地低下,两手不自然地捏着带着许多补丁的上衣的衣角。不知是因巴山的寒冷,还是因为求学的艰辛,三双小手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光泽。小屋的主人姓陈,名字却忘了,他告诉我们,学校一天吃两顿饭,上午10点,下午4点,在这个时间,他们就回到小屋自己做饭,吃完第二顿饭后,他们还要到学校上晚自习,上完晚自习后(大约晚上9点来钟),他一人再回到小屋睡觉。我问他一人住在这儿害怕吗?他不答,眼中却分明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怎能不怕呢?一个十岁的小孩孤孤零零地住在32座坟茔的边缘,四周是黑压压的大山和那长年不断的溪水哗哗的流动声响……我不禁为我的询问感到自责?也为小男孩的处境感到怜惜起来。
小男孩告诉我们,这茅屋原先是他父母亲农闲时在这儿打豆腐、压面条用的,利用农闲赚点油盐酱醋钱。后因生意萧条,关门了,便留下这座破房子和一些陈旧的设备安插在这茫茫的大巴山里。他住在这里,一是为了省掉学校的住宿费,二是为了看守房子。我知道小男孩是为了省钱才住进小茅屋的,不然,眼中怎么会有害怕与不安的神情流露!小男孩告诉我们,他太想上学了,只要父母亲让他上学,住在哪里都行。我的心不禁一颤,多么可爱的孩子啊!
怕影响孩子们吃饭上学,我们向孩子们叮吟了一些学习、安全上的事。离开了小茅屋。离开小茅屋时,三个小孩送我们至门前,挥动着三只小手,叫着“叔叔,再见”。在离开小茅屋很长距离后,我忍不住再次回头,只见三个小孩仍站在门前,他们见我回头,又再次向我挥着三只小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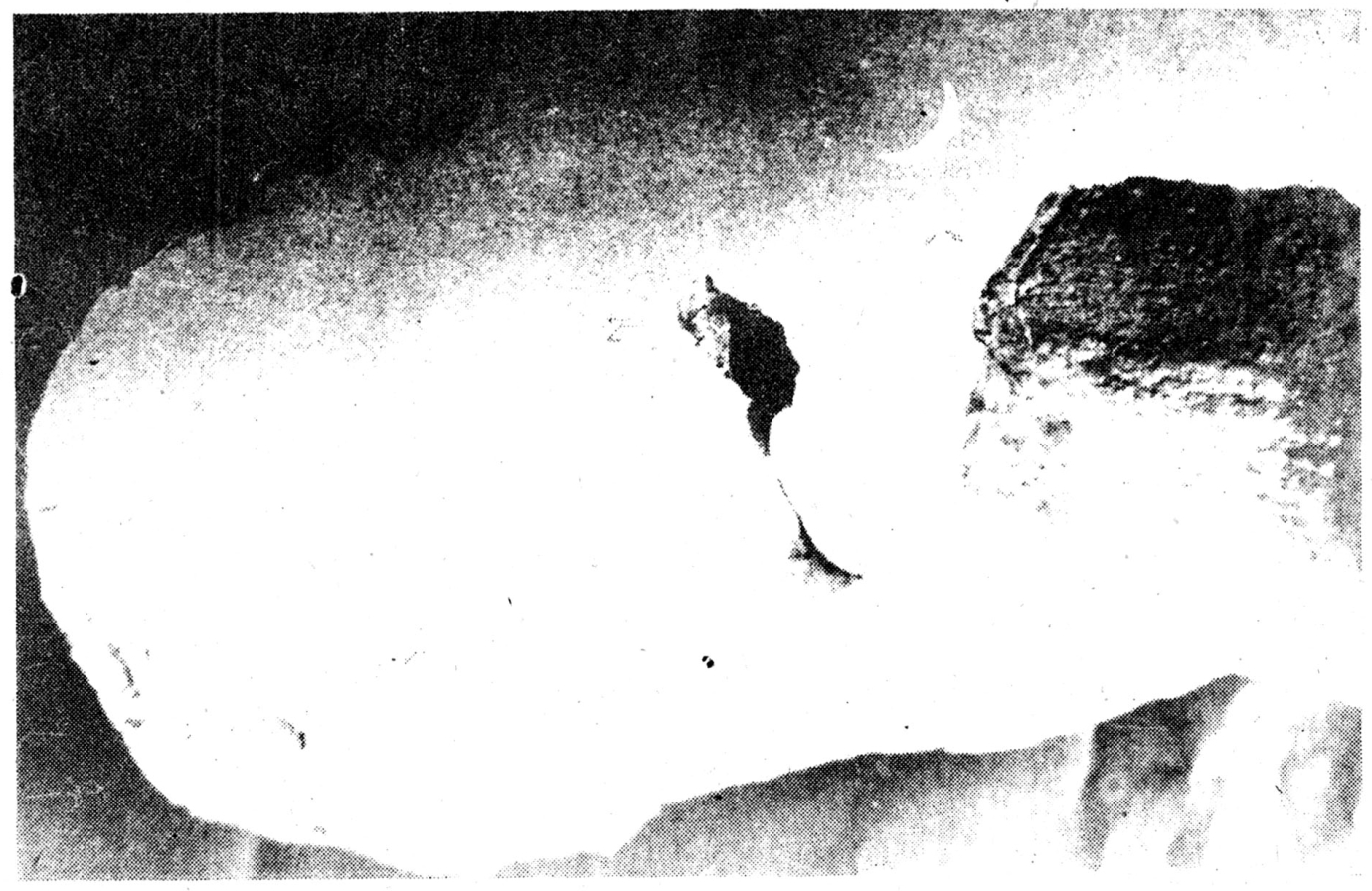
举头望明月 章年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