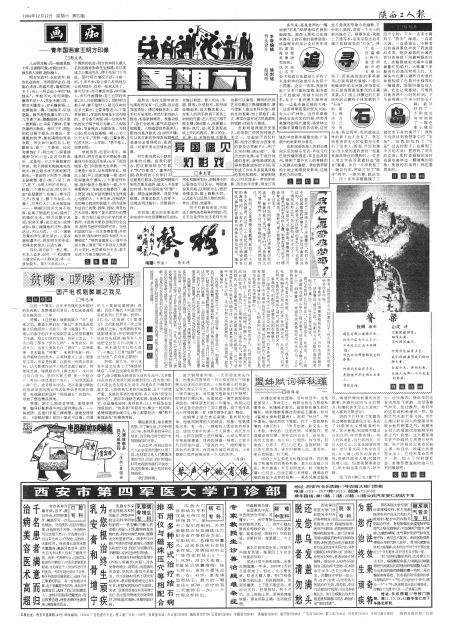
画痴
——青年国画家王明方印像
□郭义民
人云明方痴,而一痴竟是数十年,且痴得可爱,亦痴出水平。故尔有人戏称:画坛痴人。
明方生农村,长在农村,根也扎在农村。市师范毕业后,他痴心未改,有城不进,偏爱回到乡下,当上一所边远小学的“娃娃头”。学校不大,穷而简陋,教师不足十人,学生未满三百。明方不嫌其小,亦不嫌其陋,上完课独居一隅,习画练字,乐哉悠哉。教书是件挺累人的工作,几节课下来,腰酸腿疼,但只要一想到画,立马来了精神,苦累亦烟消云散矣。每日下午,西坠的红日悬于枝头,抖落出一串清脆的铃声,激起满园的笑语欢歌。师生如归巢的鸟儿,眨眼散去,留下一片静寂。他匆匆填饱肚子,跨出校门,踩着铺满野花的小径,走进田野深处。这是他一日之中最惬意的时刻。他手持画板痴痴地站在地头,画山画水画天画地画花画鸟,一直画到夕阳西下,接着去画晚霞、暮日,痴了,呆了,疯了,狂了,为常人所不可思议。眨眼几个春秋过去,明方的斗室“金屋藏娇”:东墙上,牵牛花儿开;西墙上,棚下吊金瓜;北墙上,豆荚扛大刀,玉米抱娃娃……一幅幅田园风光美不胜收,拓展了陋室的空间,滋润了枯燥的生活。明方沉醉于其间,闲来无事,或立或坐,或倚或卧,细心揣摩他的习作,通宵达旦,不以为苦。一日,一通晓丹青的学生家长来访,入室观画惊喜不已,抓住明方的手说:若得名家指点,必成大器。
自此,明方添了一桩心事。然名人虽多,但对一个木讷憨厚不喜交际的小人物来说,寻一人犹如登天。苍天不负有心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明方有幸同久慕大名的国画家张皓先生相遇,并以虔诚之心感动先生,拜于先生门下为徒。那时明方境况不好,斗室一间,十多平米,除公家几件供他办公的用具外,仅有一张双人床了。桌可写字,亦可擀面沏茶;床可睡人,亦可作画摆物;若三五同好来家,主人只好顺墙而立。那时明方教小学,妻干临时工,每月仅有的百多元薪水,上要孝敬老人,下要养家糊口,学画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幸亏苍天有眼,将一位知冷知热的女子赐予明方为妻,二人相依为命,节食缩衣,为画而苦。为明心志,明方自拟条幅一帧,上书十六个大字:“苦熬十载,三餐食素,但求不死,一心学画。”悬于壁上,自律自励。
学画虽苦,但苦中有乐。每逢周日,明方总是天不亮起身,蹬着自行车往返百余里,从乡下赶到城里,登门向张皓先生求教,一气儿竟是十余年,从未间断学业。每次上城,早上在家饱餐一顿,走时兜里塞两个馒头,上午看老师作画,饭时躲进小巷凑合一顿,下午再看再学。张皓先生被感动了,逢人便说,他从未碰到像明方这样痴心为画的人。十多年来,在张皓先生的精心栽培和扶植下,明方逐渐形成自己典雅、敦厚、洒脱、秀美的艺术风格,博得了美术界同行的赞誉。明方现已是市55中学的美术教师、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陕西书画研究院研究员。当他的国画作品一次次参赛参展,并相继获得“蒲松龄杯国际书画艺术大赛银奖”、“陕西省建党七十周年书画大赛三等奖”等十多项令人羡慕的大奖时,他同妻相对无言,禁不住流下百感交集的热泪。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