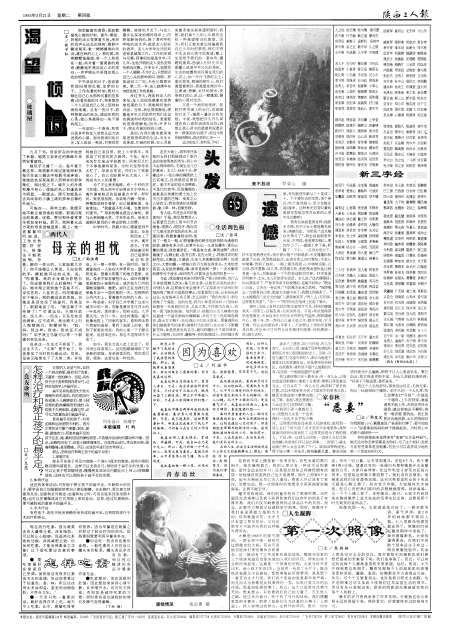
母亲的担忧
尚洪涛
九月下旬,母亲所在的学校放了秋假,她搭父亲单位的顺路车来西安看望我。
她似乎又瘦了一点,每年夏天都这样。高原紫外线过度地照射及每天往返三趟去学校教书地奔波,使她脸色呈现高原人所特有的那种微红。相比较之下,城市人的冷漠和漫不经心,使她的热心和谦恭更为明显。一眼望去,便可知她是从古风尚存的小镇上来的那种自尊的外地人。
可能在一、两年之前,我便开始不敢正视母亲的双眼。那里闪现出的焦虑、忧郁,责问和怜爱常常令我如坐针毡。那天,我陪着从远方来的母亲进城逛街。路上,她一直絮絮叨叨地说,工作当然要好好干,结婚也不能耽误啊。你看,跟你一样大的,人家娃都几岁了。你不结婚让人笑话。又拉拉我的手,撩起她耳边的头发。说:“你看看,我的头发都为你愁白了。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随后,她非得让我给她个答复不可。说实在的,人各有志,何况婚姻还在于缘分,我的确没法回答她。但她还是没完没了地逼问。我真急了,狠狠地说了句:“我这辈子不结婚了!”盯着远处,只顾往前走。没几步,一回头,只见母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也顾不上行人频频侧目,躬腰陪笑:“妈,妈,别这样,我结,我结还不成吗?”似乎我立马就可以带一个新媳妇来见母亲。
母亲这一生也太不容易了。我出生不久,“文革”便开始了。母亲参加了当时的社教运动。后来,母亲又陆续生下了大弟二弟,并坚持她自己亲自带。我上小学那年,母亲成了村里的民办教师。于是,每天匆匆忙忙地去学校教书,回家后又忙个不停地操持家务。当时只觉得母亲太忙了。母亲也常说,你们大了我就省心了。自己也盼着早长大成人,不再成为大人的累赘。
为了不让我多跑路,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从初中开始便由乡中学转人离外婆家较近的县城重点中学。那时间,家里很拮据。母亲每月磨一袋面,将精面送到外婆家,自己留着粗面。母亲常说:“我就是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们读书。”母亲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我与大弟相继大学、中专毕业后,母亲又送部队复员的小弟去财院上自费。
中学时代,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外面去。及至到西安上了大学,离开故乡,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那样地恋家思母。大一第一学期,有一段时间,每天黄昏独自一人坐在大学草坪边,望着夕阳发呆,想着太阳落下的地方是家。此刻,母亲不知在做些什么,或许在辅导邻居家的小孩做作业,或许在大门外的菜畦里锄草、施肥,或许正在为我们兄弟做冬衣……国庆前的一天,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看着窗外如织的人流,心中一阵悲凉,似乎自己并非属于这座大城市中的一员,而象是漂泊在汪洋中的一叶孤舟,那样渺小,那样无助,几乎要沉没。次日一早,也没有请假,毫不犹豫地搭上了回家的客车。看到西北那片荒寂的高原,看到了高原上的家,看到了家里的母亲,我的心里一下子踏实起来。返回单位后,再也不觉得神不守舍了。
如今,我长大成人走上社会了,却并没让母亲省心,反而因婚姻增添了母亲新的烦恼。母亲因爱而忧,我因爱而烦。原来,这爱也是一种负担。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