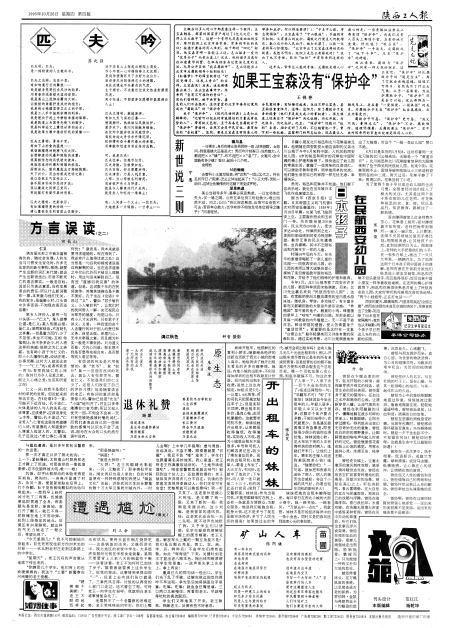
方言误读(之二)
田长山
仁义
语言是无形之中被丰富被淘汰的。随社会发展,人的生活与习惯发生变化时,许多无法容纳的新生事物、感情,就要产生出新的词汇来代替,就会产生出新语迭出、旧语不断死亡的语言事实。一般老百姓,说话只为表达意思,没有发展语言的责任,所以什么新词轰炸一事,本来就与他们无关。我的家乡,是偏僻小村,口头语中许多话语,不知现在是否还活着?
家乡人评价人,爱用一句口头语——“仁义”。某人做事公道,是仁义;某人知恩必报,是仁义;某两家结亲,不言财礼之多寡,一切是量力而行,少了不见怪,多也不可能,互相你推我让,决不争多论少,村人将这样的亲戚,统称之为仁义亲戚。也有称小孩子为仁义的,即小小儿懂得礼貌,说话在理,办事灵醒,这时大人就说这孩子——“仁仁”的,或者再奖赏一两句:看把我娃仁的心疼的!取其行为令人见爱之意。能让人心痛之爱,也见其所爱之深!
仁义一词,自然不是我们村的草民的发明。但论起来却相当古老。在《论语》中一查,可能不下近百处。孔子说仁,大体是讲的人与人的关系,应该尊重,应该爱护,应该设身处他等等。譬如,孔子说过,“仁者爱人”,仁者在这里当有道德的人讲,有道德的人知道爱护人尊重人体谅人的。又譬如,孔子还说过,“求仁得仁,吾复何忧?”意思是,我本来就是要寻求道德的,现在得到了,我还有什么值得忧虑之处?这当然是一句自我标榜或者说是自我解嘲的话,当在追求道德之中付出代价而不被世人理解时,用这句话来解脱自己,很有些“道德自我完善”的味道。但是,这词数千年的在民间流传,其情其境确也是不算不美好。孔子也在《论语》中说过“义”,譬如“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让我们村的民间哲人一解,决无视民众为草芥的揣度,而是以为,只有小人才光讲利,只有君子才讲义。义者,一种自觉的由个人去履行的对于别人的责任和义务,自觉去做,深埋内心,无半点牵强之意,而且颇为朴实一般是不事张扬,只为道义而做,为内心而做,根本想不到是否要等电视台来,是否要等别人看见等等。
有些词的死去是不用惋惜的,象“老爷”、象“奴仆”象……但是有些词的死去,就让人有些想凭吊。譬如仁义,不知是我们的仁义少了,还是人们改变了自己的评价习惯?但是随着语言的变迁,有些词的复活却是很惊人的,譬如已经是“先生”“小姐”地叫开了,并且以多带港澳台口音为荣,所以又杞人忧天一回,不知会不会有一天只有些被艳羡被时髦的词汇,而我们连表达自己的一些细致的感情与认识也不会了选词,因为在大众的口头的流行语中没有。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