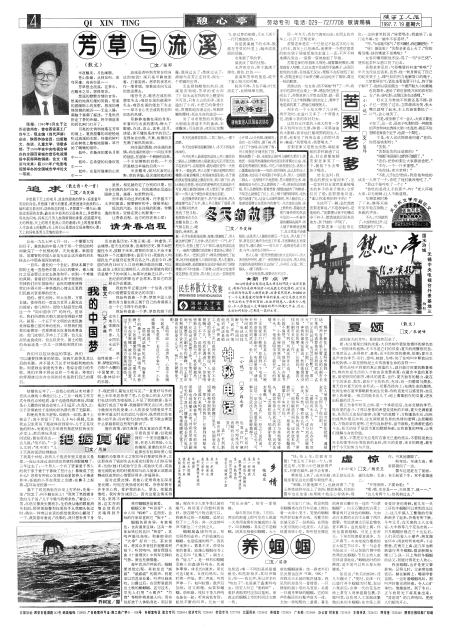
本版导读
养蝈蝈
文/苗源
我对蝈蝈甚是喜爱。
蝈蝈又称“叫哥哥”,关中人叫“蚂蚱”,在西安,会玩的行家却直称它“板子”。
蝈蝈色彩各异,有黄褐色,也有通身豆绿,还有一种体如铁红的名日“铁哥”,其鸣声雄壮高吭,和秦腔里的“大净”好有一比。茶余饭后,将其众多者挂於屋檐或树枝下,听其鸣叫,颇有琵琶乐曲《十面埋伏》中两军交锋的气势,倒也充满情趣。
每年农历芒种前后,蝈蝈便首批出现,其初发出“戚戚”“戚戚戚”的弱声,到夏至以后直至处暑,叫声日趋高吭。白露过后,在田野里捉到出土晚的嫩蝈蝈,还可过冬。早先人们用“小葫芦”“竹筒”等物件将其装入内,用布包好放于人体贴身处,用以保暖;现在不少人家冬季已装有暖气,将其笼子用塑料袋装好,放在暖气片附近就可以。我曾养过的一只蝈蝈,虽然已到了十二月份,其一次连续叫声不断达二十分钟之久。
蝈蝈属螽蟖科鸣虫。和它同类的还有,产於临潼的山蝈蝈,也是临潼的特产,因其产地狭小,数量不多,很受玩家的喜爱,临潼山蝈蝈在书上的正名叫“扎嘴儿”,南方人称“姐儿”,是一种形似蝈蝈而略小的螽蟖科鸣虫,其通体翠绿,体长约3厘米,须长可达5厘米,日夜均鸣叫,叫时第一声低,第二声高,叫两声停一下,初叫较慢,数声后加快,后又渐慢,如果和蝈蝈、纺织娘、吱拉子等几种鸣虫挂在一起,听其高低有别,起伏不断的叫声,尤如一场“民乐合奏”,别有一番情趣。
每年阳历6月底,7月初,西安的街道上即可见有人挑着一大串用高粱杆皮编成的小笼子,叫卖蝈蝈,其实它不是蝈蝈,因其长相极似蝈蝈,大小也相近,唯一不同的是其复翅极长,和尾部相齐,其叫声嘶长,吱……的长声,所以学名叫“吱拉子”,也是属于螽蟖科鸣虫,西安人叫它“麦蚂蚱”,爱好者购买时应加以鉴别。而真正的蝈蝈上市的时间比它晚一些。
在天安门广场,我见到那卖蝈蝈者在自行车后座上绑扎着一大串小笼子,笼里的蝈蝈鸣声好似重声合唱,为繁华的京城又添了一份热闹;在西安大麦市街的小吃夜市,人们品味着风味小吃,聆听挂在摊位前的蝈蝈演奏,使一群老外们见此景也连声“OK、OK!”在陇东天水城的鞋匠铺里,我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一只精制的超小型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通身翠绿的蝈蝈,它的叫声和鞋匠的钉鞋声溶为一体,尤如一场短暂的二重奏。著名的青田石雕中有一佳作“白菜蝈蝈”,白玉石雕成的白菜上攀着两只豆绿色的蝈蝈,尤如洁白无瑕的玉石中点缀了两只翡翠,传说慈禧太后见此物也爱不释手;宣统皇帝上朝,怀里也揣着蝈蝈,可见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喜爱者甚多。九三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正大综艺节目中,有一与会者当场出示一只从保温竹筒中悠然爬出的蝈蝈,节目主持人赵忠祥诙谐地说:“蝈蝈此时的珍稀度,是不是可以和大哥大相媲美。”
俗话说:“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现时,京津一代以盛行养冬蝈蝈为时髦。农历小寒前后,京津一代的花鸟市场上常有人用保温箱包裹,手提叫卖,这些用人工加温法繁殖出来的冬蝈蝈,在市场上很受爱好者的青睐,前几年一只上好的冬蝈蝈可以卖到百元以上,这几年搞人工繁殖的行家渐渐多了起来,价格有所下跌。今年元月,在天津的工人文化宫,大丰桥等几个花鸟市场,一只冬蝈蝈价格在三十元左右,人们买后装入小葫芦,将其揣在怀中,闲余时听其鸣声,十分惬意。在南方上海,近几年也渐渐盛行养冬蝈蝈,据说新婚女婿上门,送一只上等的冬蝈蝈给岳父,很能讨得老丈人欢心。
我爱蝈蝈,也许是受父辈影响,记得儿时,父亲常在晚饭后,躺在躺椅上,嘴里哼着京剧,一边听着蝈蝈鸣叫,那叫声好像京胡伴奏,令人心旷神怡,情趣盎然。到了冬日,正午的阳光下将其拿出来,“哥哥哥”的几声鸣叫,更使人们颇为开心。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