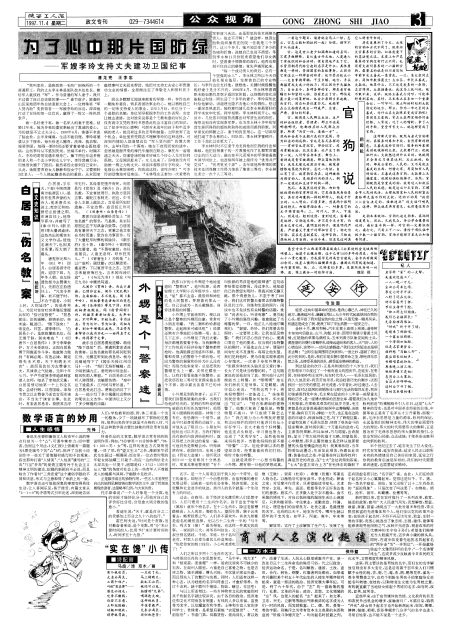
数学语言的妙用
先锋
鲁迅先生曾把庸俗文人张资平小说的特点归结为一个“△”,可谓辛辣有力,切中要害。仿照这个用法,《文汇报》上曾载有一篇题为《漂亮旗号下的“△”》的,批评了当前小说创作中一些关于爱情题材描写的不良现象,指出那种打着“人情美”、“人性美”旗号的“三角”乃至“多角”的爱情主题有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拟题的新颖自不必说,而且暗含了作者对“三角恋爱”这个庸俗字眼的不屑和厌恶。形式与立意取得了神韵上的一致。
数学语言还可借助深奥的事理变得具体生动,让人喜闻乐见,易于接受。有篇文章从“3-1=0”的矛盾等式引申论述,深刻地告诉人们,学校教育的德、智、体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少了一项就破坏了事物的完整性,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不合格的人材。可见这种数学语言要比抽象的理论更有说服力。
科普作品的文章里,数学语言常有独到的说明作用,例如:“3分钟笑=15分钟体操”、“96.9:100=男:女”等,这样的表达方式简明易懂,一目了然,有“望文生义”之妙。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画过一幅漫画:饭店里,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女郎独霸三只凳子,而在一边的两位老太太却共坐一只凳子,画题是《1:3与2:1》妙在从人“数”的角度对社会上的一些青年人不尊敬老人的揭露与讽刺,于幽默中见批评。
正是数学语言的独特作用,一些名人学者便把自己的独到见解熔铸在数学语言文中,富于哲理地展现给读者。这里略举几例,与大家共赏:
托尔斯泰说:“一个人好象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的值愈小。”
爱迪生说:“天才,就是百分之二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八的血汗。”
雷巴柯夫说:“时间是个常数,但对勤奋者来说,是个变数。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来计算时间的人,时间多五十九倍。”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