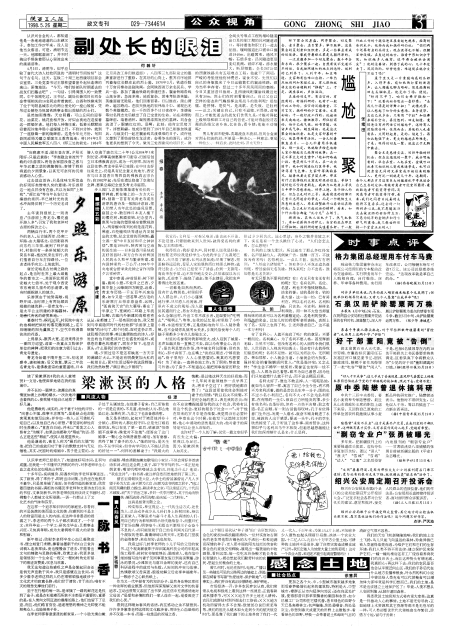
本版导读
夕照乐游原
廖代谦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这首流传千载的《乐游原》,将饱含家国没落之感与年华迟暮之悲的满腹惆怅,寄情于辉彩将逝的夕照景象,以其无可奈何的沉绵哀感动人心弦。
过去读这首诗,只是体味它所营造的好则好矣惜难久矣的意境,对乐游原这一地点并没有在意。只以为如同“上林苑”、“曲江池”等当年长安仕女嬉游的场所,早已被时光的流水冲淘得仅剩下一个历史名词了。
去年读到报纸上一则消息:“乐游原上青龙寺,樱花盛开游人多”,引发了我和老伴对古原的探访之心。
两辆自行车,两个花甲开外的老人。从古城西郊,经南二环路,由大雁塔北,沿西影路再向东约三华里,就到了铁炉庙村。村巷间有一条斜坡颇大的简易车路,拖拉机来往穿行。我们推着自行车打探路径。一位老者扬手向北:上坡就到。
唐长安城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其面积比明西安城大七倍半。处于现今西安市东南郊几里外的乐游原,是当时颇招游人的地方。
乐游原由于地势高敞,视野开阔,当时原上有两处颇具规模的建筑群,一是青龙寺,一是太平公主所建的亭阁园林,是唐代有名的游赏胜地。
暮春时节,桐花正开。村民院中高大的泡桐树把缤纷的落花撒到路上。在午后暖暖的阳光薰照之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上得原头,眼界大宽。还没来得及作一番四方巡望,迎面一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牌,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青龙寺遗址。
青龙寺始建于隋开皇二年,初名灵感寺。唐初被废,后又恢复。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是佛教密宗的重要道场。日本僧人空海于唐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来到长安,师事高僧惠果学习密宗,归国后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成为一代宗师。因为有这段往事,青龙寺虽早已废毁,在中日友好往来史上,仍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西安市与日本国香川等四县的佛教真言宗合作,自1982年起,先后在遗址修建了空海纪念碑、惠果空海纪念堂及青龙寺庭园。
步入园门,左侧依围墙建有长长的一带碑廊。嵌在墙上的一方方大石碑,刻着一首首有关青龙寺或乐游原的唐诗及一幅幅诗意画,把人们带入当年此处的盛况旧景。庭园之中,数百株日本友人植下的樱花树,展霞披锦。纪念堂内,惠果与空海的塑像端坐着默视游人,两旁橱中陈列的则是莲花砖、佛座、石经幢残块等遗址内发掘出的文物。纪念堂前的西南侧,矗立着一座“中日友好和平之钟钟楼”,那是1994年,陕西省与空海的诞生地——日本国香川县结成友好省县时,双方合作为祈两国人民的永久和平与繁荣所建。楼内悬钟重约一万公斤,1996年中央电视台曾采录此钟之音作为除夕吉祥钟声。
堂中参谒,碑前留影,树下野餐,廊间小憩,不觉日之已西。夕照中登上云峰阁四方眺望。近看,青龙寺历经一千五百年兴废沧桑,如今又是一团苍翠,把古老的乐游原打点得春意盎然。远眺,“孤高耸天宫”的大雁塔,落在了半原之下,宽阔的二环路上车流如鲫,古城内外新建的高楼密密丛丛,全都镀上了一层亮丽的金色。我又想到与李商隐同时代的杜牧那“乐游原上望昭陵”的诗句了。那个时候,面对党争正烈、战乱频仍的世事,难以施展抱负的诗人,抒发出的也只能是或对已往盛世的追怀,或感苍茫暮色的湮逼了。同在夕阳下,也登古原头,什么是我们的诗情呢?
哦,夕照过后不是还有映亮一方天宇的满城灯火么,不是还有明晨更加火红的一轮旭日么,面对生活过程中的这段辉煌,我们欣然咏赞:“满目青山夕照明”!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